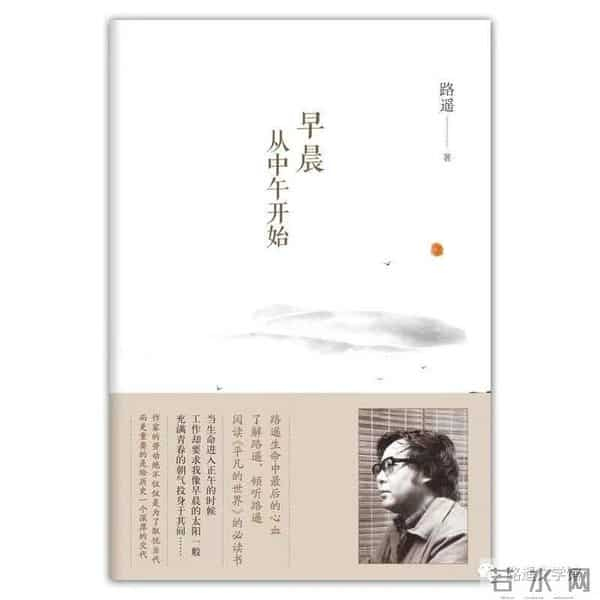我给山区孩子捐款十年,一次去探望,发现钱全进了校长口袋
我叫林森,三十八岁,在上海开一家半死不活的设计工作室。
单身,没娃,钱不多不少,日子不好不坏。
唯一的“善举”,是给一个叫“云顶”的山区小学捐款。
坚持了十年。
这事儿开始得很偶然。十年前,我刚创业,赚了第一笔还算可观的钱,年轻,有点烧包,总觉得该干点有意义的事,来证明自己不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网上随便一搜,就看到了云顶小学的求助帖。
照片上,黄泥墙,黑瓦片,孩子们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脸蛋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的心,就那么被戳了一下。
联系了帖子上留的校长电话,一个姓王的男人,声音听着很朴实,带着浓重的方言,一口一个“感谢领导关心”。
我说我不是领导。
他嘿嘿地笑,说,给娃儿们带来希望的,就是领导。
我被他这句话给说服了。
于是,每个季度,我都会雷打不动地打一笔钱过去。
一开始是几千,后来工作室效益好了,就加到几万。
十年,算下来,不多不少,也快一百万了。
王校长每年都会给我寄“工作报告”。
几张照片,孩子们穿着新衣服的合影,新修的篮球架,新买的图书。
还有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字迹很笨拙,但感情充沛。
我把这些信都收在一个盒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觉得自己这十年,总算干了件人事。
我从没想过去实地看一看。
一来是忙,工作室离了我玩不转。
二来,我有点怕。
怕什么?怕亲眼看到那份贫穷,会让我觉得自己的捐助杯水车薪,产生无力感。
也怕,那份淳朴只是我的想象,去了,滤镜碎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
人到中年,守着一点天真不容易,我不想亲手打碎它。
就这么隔着十万八千里,当个赛博慈善家,挺好。
直到上个月,我收到王校长的一封邮件。
这很反常。
以前他都用微信,发几张图,说几句感谢的话。
这封邮件,写得极其规范,标题是“关于云顶小学2023年秋季学期发展规划及资金缺口报告”。
附件里是一个做得相当漂亮的PPT。
数据图表,SWOT分析,发展蓝图……一应俱全。
我一个做设计的,都得承认,这PPT水平不低。
但问题是,这太他妈不对劲了。
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山村校长,能做出这种东西?
我把PPT放大,看到了右下角一个极小的logo。
是上海一家挺有名的咨询公司。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感,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
我回拨了王校长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林老板啊!邮件收到了吧?我们这也是与时俱进,请了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想把学校搞得更正规一点!”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带着点谄媚的笑意,但听起来,油滑了不少。
“王校长,这PPT做得真好,得花不少钱吧?”我试探着问。
“哎呀,都是为了孩子们嘛!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也是勒紧裤腰带……”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教育经”。
我没听进去。
我只觉得,我盒子里的那些手写信,瞬间变得有点可笑。
挂了电话,我盯着电脑屏幕,那份精美的PPT,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我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我做了个决定。
去云顶。
十年了,该去看看我那些“星星”了。
我没告诉王校长。
买了张去昆明的机票,然后转火车,再转长途汽车。
一路颠簸,越走越荒凉。
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低矮平房,最后,只剩下连绵不绝的大山。
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泥土和植物混合的潮湿气味。
这味道,很陌生,但又让人心安。
三天后,我终于到了云顶乡所在的县城。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街道还算整洁,有几家看起来不错的酒店。
我在县城住了一晚,找了个当地的司机,包他的车上山。
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本地人,姓张,话不多,皮肤黝黑。
我递给他一根烟,跟他闲聊。
“师傅,去云顶小学路好走吗?”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老板,你去小学干啥?考察?”
“哦,我以前资助过那里的学生,来看看。”
他“哦”了一声,语气有点意味深长。
“那里的王校长,是个能人啊。”
“能人?”我心里一动。
“是啊,”小张师傅吐了个烟圈,“我们这山沟沟里,就属他混得最好。县城里有两套房,开着一辆帕萨特,儿子都送到国外读书了。”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
帕萨特?
儿子出国?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一个小学校长,工资很高吗?”我的声音有点发干。
小张师傅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点本地人特有的狡黠和了然。
“工资?老板,你开玩笑吧。我们这儿,死工资能干啥?王校长路子野,会拉赞助,会搞项目,上面下面关系都通。不然你以为呢?就凭那几间破瓦房?”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车子开始盘山。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
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
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我只觉得冷。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
车子在一个岔路口停下。
“老板,前面车开不进去了,得走进去,大概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
我付了车钱,背上包,下了车。
小张师傅看着我,欲言又止。
“老板,你是个好人。”他最后说,“但有些事,别太较真。水至清则无鱼,懂吧?”
我没说话,朝他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那条泥泞的山路。
懂。
我怎么会不懂。
可我那一百万,不是用来养鱼的。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刚下过雨,路上全是烂泥,一脚深一脚浅。
我那双在上海只用来走地毯和地板的皮鞋,很快就面目全非。
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滑倒。
等我浑身是泥,气喘吁吁地看到“云顶小学”那块歪歪扭扭的木牌时,已经是中午了。
学校,和我十年前在照片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几排低矮的黄泥房,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的土坯。
操场就是一片泥地,中间立着两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
没有篮网。
唯一的变化,是墙上用红漆刷着一行大字: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助!
那红漆很新,刺眼得很。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幅景象,心里五味杂陈。
说不上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
或许,是我一开始就想错了。
一百万,十年,摊到这么个穷山沟里,可能真的连个水花都见不着。
也许王校长是贪了,但贪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用到孩子们身上了?
比如,孩子们的午餐,书本,衣服?
我开始为他找理由。
我宁愿相信他只是个有瑕疵的好人,而不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为如果他是骗子,那我这十年,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是个女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粉色外套,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手腕。
脚上是一双破了洞的帆布鞋,脚趾头都快顶出来了。
她跑到操场边的水龙头下,拧开,把脸凑过去喝水。
水龙头的水流很细,她喝得很急,水溅湿了她的衣领。
我看着她,心里那根刺,又开始疼了。
我走过去。
“小朋友,你好。”
她吓了一跳,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和我十年前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清澈,明亮,像山涧里的泉水。
只是,多了几分怯生生。
“叔叔,你找谁?”她的声音很小。
“我来找你们王校长。”
“哦,校长去镇上开会了。”
“开会?”我愣了一下,想起小张师傅的话。
“是啊,校长经常去开会。”女孩说,“开着他的小汽车。”
小汽车。
我心里的那点侥G幸,彻底没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
“我叫阿雅。”
“阿雅,你脚上的鞋……破了。”
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鞋,有点不好意思地把脚往后缩了缩。
“没事,还能穿。”
“叔叔给你买双新的,好不好?”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渴望,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她摇了摇头。
“为什么?”
“奶奶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我心里一酸。
多好的孩子。
我从包里拿出一袋带来的巧克力,递给她。
“这个不是给你的,是给所有小朋友的。你帮叔叔分给大家,好吗?”
她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说了声“谢谢叔叔”,然后转身跑回了教室。
很快,教室里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和欢呼。
我笑了笑,心里却更堵了。
我绕着学校走了一圈。
教室的窗户,很多玻璃都破了,用塑料布糊着。
课桌椅,东倒西歪,缺胳膊少腿。
所谓的“图书室”,就是一间空屋子,靠墙立着两个空荡荡的书架,上面积满了灰。
我那一百万,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走到学校后面,那里有一排新盖的房子,红砖墙,看着很扎眼。
一个老师模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找谁?”
“我找王校长。”
“他不在。”那老师的语气很冷淡,上下打量着我。
“我是来捐款的。”我撒了个谎。
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哎呀!贵客!快请进,快请进!王校长去县里给孩子们跑项目去了,马上就回来!”
他把我让进其中一间屋子。
我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王校长的办公室,兼宿舍。
装修得和外面的破败截然不同。
地板是光亮的木地板。
一套红木的办公桌椅,擦得锃亮。
墙上挂着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
角落里,摆着一个精致的玻璃柜,里面全是名烟名酒。
最刺眼的,是桌上那个相框。
相框里,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男人,站在一所国外的大学门口,笑得很灿烂。
旁边,站着一个满脸红光,挺着肚子的中年男人。
是王校长。
我认识他。
虽然只是在照片上。
但比照片上,胖了,也油腻了。
“林老板,您先坐,喝茶!”那个老师热情地给我倒水,“我姓李,是这里的教导主任。”
我没坐。
我指着墙上的照片,“这是王校长的儿子?”
“是啊!”李主任一脸骄傲,“有出息啊!在澳大利亚留学呢!一年学费生活费,几十万呢!全靠王校长一个人,不容易啊!”
几十万。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终于知道我的钱去哪儿了。
它们变成了这套红木家具,变成了这满柜子的名烟名酒,变成了王校长儿子在澳大利亚的阳光、沙滩和学位。
而阿雅,还穿着那双露着脚趾的破鞋。
我没有发作。
我平静地对李主任说:“我出去走走,等王校长回来。”
我走出了那间令人作呕的办公室。
我需要冷静。
我沿着村里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
这个村子,是真的穷。
大部分都是土坯房,零星有几家盖了砖房的,也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路边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走到村口一棵大榕树下,一个正在纳鞋底的老奶奶叫住了我。
“后生,城里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
“来找王校长?”
看来王校长在这里,是名人。
我“嗯”了一声。
老奶奶叹了口气,手里的针线活没停。
“他家那新盖的二层小楼,就在村东头,最气派那栋就是。你是不是给他送钱来的?”
我没说话。
“唉,”老奶奶摇了摇头,“你们这些城里人,心眼好,就是太实诚。那钱,到不了娃儿们手里的。都进了他的无底洞了。”
“没人管吗?”我忍不住问。
“管?谁管?怎么管?”老奶奶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他上面有人,下面有亲戚。这村里,一半人都姓王。我们这些外姓人,说句话都没人听。”
“前几年,有个年轻老师,刚分配来的,有正义感,想去县里告他。结果呢?没几天就被调走了,听说调到更远的山沟沟里去了。”
“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说话了。”
老奶奶低下头,继续纳鞋底。
“我们都盼着他早点遭报应。可这老天爷,有时候也瞎了眼。”
我的心,彻底凉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回到学校门口。
一辆黑色的帕萨特,闪着光,从山路那头开了过来,稳稳地停在校门口。
车门打开,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
穿着一件体面的夹克,手里夹着一个公文包。
他看到了我。
愣了一下。
然后,脸上立刻堆起了我无比熟悉的、热情的笑容。
“哎呀!林老板!您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去县城接您啊!”
他快步走过来,伸出双手,想握住我的手。
我没动。
我看着他。
看着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看着他手腕上那块闪闪发亮的金表,看着他身后那辆和我捐款总额的零头差不多价钱的汽车。
十年。
我隔着电话和照片,和他打了十年的交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人。
他,就是王德发。
云顶小学的校长。
一个靠吸孩子们血的蛀虫。
王德发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林老板,一路辛苦了!快,快里面请!李主任!赶紧把我那罐最好的龙井泡上!”
他热情地揽着我的肩膀,想把我往里带。
他的手很胖,很软,带着一股烟酒和劣质香水混合的味道。
我感到了生理性的恶心。
我轻轻挣开了他的手。
“王校长。”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我来,就是想看看。”
“应该的,应该的!”王德发连连点头,“您是我们学校最大的恩人,来看看是应该的!我们学校这几年变化可大了,全靠您的支持!”
他指着那排破烂的教室。
“您看,这墙,我们去年刚粉刷过!还有这窗户,也都换成新的了!”
我看着那些用塑料布糊着的窗户,想笑。
“是吗?”我说,“我看着,怎么跟十年前的照片上,没什么两样?”
王德发的脸色又是一僵。
“哎呀,林老板您有所不知。我们这山区,条件差,风吹雨淋的,东西坏得快。这不,我们正准备申请一笔资金,把整个教学楼都翻新一下呢!”
他把我带到操场中央。
“您看,这篮球架,也是您捐的钱买的!孩子们可喜欢了!”
我看着那锈迹斑斑,连篮网都没有的铁架子,沉默不语。
一个穿着破鞋的阿雅,和一对没有篮网的篮球架。
多么绝妙的讽刺。
“走,林老板,我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多媒体教室!”
王德发好像完全没感觉到我的冷淡,依旧兴致勃勃。
他把我领到一间锁着的教室门口,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房间里,靠墙摆着十几台崭新的电脑,显示器上还蒙着塑料膜。
“您看!”王德发一脸骄傲,“这都是最新款的!有了这些,孩子们就能跟城里的孩子一样,上网学习了!”
我走进去,摸了摸其中一台电脑。
上面一层厚厚的灰。
我按了一下开机键。
没反应。
“这个……电路有点问题,还没接上电。”王德发尴尬地解释,“山里条件就这样,您多担待。”
我点了点头。
“挺好的。”我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戳穿他?
当着那个一脸崇拜地跟在后面的李主任的面?
我不想。
我觉得那太便宜他了。
“林老板,您看,天也晚了。我已经让镇上最好的饭店留了包间,咱们先去吃饭,接风洗尘!”王德发热情地拉着我。
“不用了。”我拒绝了,“就在学校吃吧。我想尝尝孩子们的伙食。”
王德发的表情,瞬间变得很精彩。
像是吞了一只苍蝇。
“这……这怎么行!您是贵客,怎么能吃食堂呢!食堂那伙食,粗茶淡饭的,怕您吃不惯。”
“我吃得惯。”我坚持,“我捐的钱里,有一部分,是专门的伙食补贴,对吧?我就是想看看,孩子们每天都吃些什么。”
我的语气很平淡,但态度很坚决。
王德发和李主任对视了一眼,眼神里有些慌乱。
“那……那好吧。”王德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就是简陋了点,您别嫌弃。”
学校的食堂,就是一间搭出来的棚子。
几张长条桌,几条长板凳。
晚饭很简单。
一人一个黑乎乎的玉米面馒头。
一碗看不见一点油花的白菜土豆汤。
孩子们排着队,默默地接过自己的那一份,然后找个角落蹲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没有一个人说话。
李主任给我端来了一份“特别”的晚餐。
一碗白米饭,一盘炒鸡蛋。
我看着那盘金黄的炒鸡蛋,又看了看孩子们手里那黑乎乎的馒头。
我把那盘炒鸡蛋,推到了旁边正在吃饭的阿雅面前。
“阿雅,你吃。”
阿雅愣住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王校长。
王德发的脸,已经黑得像锅底。
“林老板,这……”
“让她吃。”我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阿雅怯生生地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嘴里。
然后,她的眼睛亮了。
她小口小口地吃着,像是品尝着什么山珍海味。
我拿起一个玉米面馒头,咬了一口。
又干又硬,拉嗓子。
我看着王德发,“王校长,你也吃啊。”
王德发看着自己面前那碗白米饭和炒鸡蛋,一口也咽不下去。
那顿饭,我们谁都没再说话。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默。
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
山里的夜晚,冷得刺骨。
王德发安排我住在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
“林老板,山里条件不好,您就将就一晚。明天我开车送您下山。”他急切地想送我走。
我看得出来,我多待一分钟,对他都是一种煎熬。
“不急。”我说,“我还有些事,想跟王校长聊聊。”
我坐在那张红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杯茶。
是好茶。
和我办公室里一千多一两的,一个味道。
王德发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李主任识趣地退了出去,还体贴地关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开口。
“王校长,我捐了十年钱,你知道总共是多少吗?”
王德发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
“这个……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但每一笔,我们都登记在册,都用在了学校的建设上!”他立刻表忠心。
“是吗?”我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沓文件。
那是我来之前,让助理打印的所有银行转账记录。
我把它们一张一张,铺在桌子上。
“我帮你记着呢。十年,四十六笔,总共是,九十八万七千块。”
“差一万三,就一百万了。”
我每说一个字,王德发的脸色就白一分。
等我说完,他额头上已经全是冷汗。
“林……林老板……”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些钱,我们真的……真的都用了……”
“用了?”我拿起桌上那个相框,递到他面前,“用在这上面了?”
他看着相框里他和他儿子的合影,身体猛地一颤。
“用在你这套红木家具上了?用在你这满柜子的茅台和中华上了?还是用在你那辆帕萨特,和你县城里的两套房上了?”
我一句一句地问,声音越来越冷。
王德发彻底瘫了。
他“扑通”一声,从沙发上滑了下来,跪在了地上。
“林老板!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我鬼迷心窍!”
他开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也是没办法啊!林老板!我儿子要出国,要花钱!我老婆身体不好,要吃药!我一个山村教师,那点死工资,我能怎么办啊!”
他开始扇自己的耳光,一下比一下响。
“我一开始没想拿这么多的!真的!我就是……就是临时周转一下,想着以后再补上……”
“可这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啊!钱来得太容易了,我……我就昏了头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演。
没有一丝同情。
我见过太多比他难的人。
我见过在工地上背水泥,一天只吃两个馒头的工人。
我见过在深夜的街头,捡瓶子补贴家用的老人。
他们都没有去偷,去抢,去骗。
贫穷,不是作恶的理由。
“补上?”我冷笑一声,“王校长,你打算怎么补?”
“你那一百万,能给多少个阿雅买新鞋?能让多少个孩子吃上一顿带肉的午餐?能把这破学校修成什么样?”
“你拿什么补?”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砸在他心上。
他不哭了。
他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他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林老板,求求你,求求你放我一马!”他开始磕头,一下一下,撞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这事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听,对不对?就说你考察完了,很满意,行不行?”
“钱!钱我慢慢还给你!我把房子卖了,车子卖了,我砸锅卖铁还给你!”
他开始语无伦次。
我看着他这副丑态,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来之前,想象过无数种和他对峙的场面。
我想过我会愤怒地咆哮,会动手打他,会把他扭送到警察局。
但真的到了这一刻,我只觉得疲惫。
和这种,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生命。
我站起身。
“王德发。”我叫他的名字,“你不用还我钱。”
他愣住了,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的钱,是捐给孩子们的,不是给你的。”
“所以,你欠的,不是我。”
我从包里拿出我的手机。
按下了录音键。
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对着他。
“现在,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对着它说一遍。”
“把你这十年,怎么一笔一笔地把捐款揣进自己腰包,怎么让你儿子出国留学,怎么买车买房,怎么看着那些孩子吃糠咽菜,自己大鱼大肉……”
“一五一十,说清楚。”
王德发的脸,瞬间变成了死灰色。
他看着那个小小的,亮着红点的手机,像是看到了地狱的入口。
“不……不要……”他瘫在地上,抖如筛糠,“林老板,你不能这样……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我就是要你的命。”
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毁了我的信任,毁了孩子们的希望,你就该付出代价。”
“王德发,你选吧。”
“是现在自己说,还是我报警,让警察来帮你回忆?”
他绝望地看着我。
足足一分钟。
然后,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地。
他开始说了。
从第一笔捐款开始。
他怎么截留了三分之一,然后是二分之一,最后,是全部。
他怎么用这些钱,在县城买了第一套房。
怎么送他儿子去了最好的私立高中。
怎么学会了喝酒,打牌,出入各种高档场所。
他说得很详细,很具体。
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活路。
说的越清楚,罪行越明确,量刑的时候,或许还能算个坦白从宽。
我静静地听着。
没有愤怒,没有激动。
我的心,像一潭死水。
他说完了。
整整一个小时。
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拿起手机,按下了停止键。
我把那段录音,当着他的面,发给了我一个在省报当记者的朋友。
然后,我拨通了110。
“喂,我要报警。”
“云顶乡,云顶小学。这里有个人,涉嫌职务侵占,金额,大概一百万。”
挂了电话,我看着瘫在地上的王德发。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
像一滩烂泥。
我没有再看他一眼。
我走出那间办公室。
天亮了。
太阳从山的那一边,慢慢升起。
金色的阳光,洒在操场上。
孩子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学校。
他们看到我,都有些好奇,又有些害怕。
阿雅也在其中。
她看到我,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依旧那么亮。
我突然觉得,我这十年,也不算完全白费。
至少,我亲手把这个蛀虫,从他们的世界里,剔除了出去。
警察来得很快。
两辆警车,从山路上呼啸而来。
王德发被戴上手铐,带走了。
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没有看我。
他的眼神,是灰败的,死的。
李主任和剩下的几个老师,都吓傻了,站在一边,噤若寒蝉。
我没有理他们。
我知道,他们或许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是沉默的帮凶。
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那是纪委和教育局的事。
我走到阿雅面前。
我蹲下来,看着她。
“叔叔要走了。”
“叔叔,你还会回来吗?”她问。
“会的。”我说,“叔-叔保证,下次回来,会给你,给所有小朋友,都带来新鞋子,新衣服,还有很多很多新书。”
“叔叔还会建一个新的学校,有明亮的教室,有真正的电脑,有可以打球的篮球场。”
“真的吗?”她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
“真的。”我摸了摸她的头,“拉钩。”
我们拉了钩。
我离开了云顶。
没有回头。
下山的路上,我接到了我那个记者朋友的电话。
“林森,你这次,可是捅了个大篓子。”他的声音很兴奋。
“是吗?”
“何止是啊!我把录音给了我们总编,总编直接上报了省里!这事儿现在是省纪委督办的案子!王德发完了,他后面那一串人,一个都跑不了!”
“那就好。”我说。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这可是个大新闻,你要是愿意站出来,你就是英雄!”
“算了。”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群山,“我不想当英雄。我就是个傻了十年的商人。”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突然觉得,很累。
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轻松。
回到上海,我大病了一场。
发烧,昏睡,做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梦。
梦里,一会儿是王德发那张油腻的脸,一会儿是阿雅那双清澈的眼睛。
一个星期后,我才缓过来。
工作室的助理小陈告诉我,云顶的事情,上新闻了。
但报道很克制,只说了某山区小学校长侵占捐款被查处,没有提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具体的金额。
我知道,这是我那个朋友在保护我。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谢了。
他回:应该的。后续有进展我告诉你。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每天忙着见客户,改方案,和甲方斗智斗勇。
上海的繁华,依旧那么真实,又那么虚幻。
只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不再去昂贵的餐厅吃饭,不再买奢侈品。
我把那些钱,都存了起来。
我开始研究公益信托,研究怎么建立一个透明的,可追溯的慈善基金。
我联系了很多律师和专业人士。
他们都说,这事儿很难,很麻烦。
我说,没关系,慢慢来。
我用了十年,养肥了一个骗子。
我想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去建一座真正能让孩子们安心读书的学校。
三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云顶乡新上任的乡长打来的。
他说,王德发的案子,判了。
数罪并罚,十五年。
没收所有非法所得。
和他有关的一批教育系统的干部,也都被处理了。
云顶小学,由县教育局直接接管,派了一个新的校长和几个年轻老师过去。
“林先生,”乡长在电话里,语气很诚恳,“我代表云顶乡三十六个村的所有老百姓,谢谢您。”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您什么时候有空,再回来看看吧。我们……我们想给您立个碑。”
“别。”我立刻拒绝了,“千万别。我不想当活菩萨。”
我挂了电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秋天的时候,我处理完了工作室的所有项目,关掉了公司。
小陈很不解。
“林哥,咱们现在势头这么好,为什么要关了?”
我笑了笑,“因为我找到了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事。”
我背上行囊,再次踏上了去云顶的路。
这一次,我没有偷偷摸摸。
我给新来的张校长打了电话。
张校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说话很实在,有点腼腆。
他亲自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到县城来接我。
去学校的路,还是那么难走。
但我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
到了学校,我愣住了。
学校还是那几排黄泥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操场上,那两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被刷上了新漆,还挂上了崭新的篮网。
教室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我看到了阿雅。
她穿着一身干净的校服,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她也看到了我,飞奔过来。
“叔叔!”
她扑进我怀里。
我抱起她,感觉沉甸甸的。
“长高了,也长胖了。”我笑着说。
张校长告诉我,王德发被抓后,县里拨了一笔专款,给孩子们换了新的课桌椅,买了新的校服和鞋子。
食堂的伙食也改善了,每周都能吃上两次肉。
那个蒙着灰的多媒体教室,也通上了电,孩子们已经开始上电脑课了。
“林先生,谢谢您。”张校长握着我的手,眼睛有点红,“您不知道,您做了件多大的好事。”
我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把一个错误,纠正了过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住在王德发那间办公室里。
我和张校长,还有另外两个年轻老师,挤在他们的宿舍里。
房间很小,很简陋,但很温暖。
我们聊了很多。
聊孩子们的未来,聊学校的规划。
我告诉他们,我打算成立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来支持云顶小学和周边山区的教育。
这个基金,会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管理,每一笔钱的去向,都会在网上公示,任何人都可以查询。
“我不要感谢,也不要功德碑。”我说,“我只要孩子们,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安心读书。”
三个年轻人的眼睛里,都闪着光。
我在云顶,待了一个月。
我和工人们一起,测量土地,规划图纸。
我要在这里,建一所新的学校。
有坚固的教学楼,宽敞的宿舍,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塑胶跑道。
我把我在上海的房子卖了。
那笔钱,足够了。
很多人说我疯了。
放弃上海的一切,跑到这山沟沟里来折腾。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
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懂。
当我看到阿雅和她的同学们,穿着新鞋,在操场上奔跑,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时。
我就知道,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
我只是一个犯过错,并且想努力弥补的普通人。
我的上半生,在追逐金钱和名利,活得像个陀螺。
我的下半生,我想为这些山里的“星星”,做点什么。
让他们,能有机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选择他们自己想走的路。
这就够了。
有一天,阿雅问我。
“叔叔,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我想了想,告诉她。
“因为十年前,叔叔在最迷茫的时候,是你们的笑脸,给了我力量。”
“所以,现在,叔-叔想把这份力量,还给你们。”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阳光下,她的眼睛,比我见过的任何宝石,都更加明亮。
我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个“王德发”。
我也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
但,没关系。
点亮一盏灯,就会有另一盏灯被点亮。
只要光亮起来,黑暗,就总会被驱散的。
对吧?
本文标题:我给山区孩子捐款十年,一次去探望,发现钱全进了校长口袋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hangye/42506.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