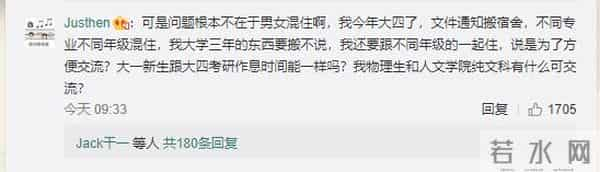男童拿现金买手机被老板哄吓拒售
六月二十五号,下午两点半。
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搅得人心烦意乱。
我死死盯着儿子李木的电脑屏幕,上面那个鲜红的数字“288”,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在我眼球上。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剩饭和汗水混合的酸腐气味,是李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的味道。
我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人用闷棍从后脑勺狠狠来了一下。
“288?”
我的声音都在抖,像秋风里最后一片枯叶。
李木,我儿子,那个我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独苗,高考成绩,288分。
他没吱声,背对着我,肩膀瘦削得像根豆芽菜。
我感觉血都冲到头顶了,后槽牙咬得咯咯响。
“你再说一遍,多少?”我往前凑了一步,试图看清那个是不是我看错了。
“爸,你不是看到了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甚至有点平静。
就是这种平静,像一瓢滚油,猛地浇在我心里那团火上。
“啪!”
我没控制住,抄起桌上的手机,狠狠砸在了地上。
屏幕瞬间碎裂成一张细密的蛛网,闪了两下,黑了。
我老婆张岚闻声从厨房冲出来,手里还拿着半截黄瓜。
“李建军!你又发什么疯!”
李木终于转过身来,看了看地上粉身碎骨的手机,又看了看我,眼睛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近乎无奈的平静。
“爸,你摔手机干嘛,分够了。”
他说。
“分够了?”我气得直想笑,指着电脑屏幕,“288分!够干嘛?够你去蓝翔开挖掘机,还是够你去新东方学炒菜?”
“够上清华。”
李木一字一句,说得清晰无比。
我愣住了,像个木雕。
张岚也愣住了,手里的黄瓜“啪嗒”掉在地上。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台老旧空调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吹出来的风都带着一股霉味。
我看着儿子那张一本正经的脸,突然觉得无比荒谬和心酸。
这孩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还是受刺激太大,精神出了问题?
我心里一阵绞痛,怒火瞬间熄灭了一半,剩下的是无尽的悲凉。
“儿子,咱不闹,啊。”我放缓了语气, trying to be gentle, “考砸了就考砸了,爸不怪你,大不了我们复读一年。”
“我没闹。”李木说,“我说的是真的,清华要我。”
我老婆张岚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摸了摸李木的额头。
“没发烧啊,孩子,你说什么胡话呢?”
“我没说胡话。”李木皱了皱眉,似乎对我们的不信任感到很不耐烦。
他这种态度,又把我的火给拱了起来。
“李建军!”张岚立刻瞪我一眼,把我即将出口的咆哮给按了回去。
她拉着李木坐到沙发上,柔声细语地哄:“儿子,你跟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网上那些招生诈骗?你可别信啊!”
“不是诈骗。”李木从他那乱得像鸟窝一样的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打印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是一封邮件的打印件。
标题是:《关于邀请李木同学参加清华大学“姚班”集训营最终面试的通知》。
“姚班?”我念出声,这名字听着怎么那么像个培训班?
“老黄瓜刷绿漆,还整个英文名,”我嘀咕着,看到下面一行小字,“Tsinghua Yao Class”。
“这是什么东西?野鸡大学的预科班?”我把纸拍在茶几上,“你为了安慰我们,编这种东西有意思吗?!”
“爸,你能不能百度一下?”李木的语气里透着一丝疲惫。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百度?我还要百度一下288分怎么上清华吗?你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清华的招生老师是瞎子?”
“李建军你闭嘴!”张岚踹了我一脚,把我赶到一边。
她捡起地上我那摔碎的手机,试着开了几次机,没反应。
“你看看你!就知道发火!手机摔了,现在想查都没法查!”她数落我。
我心里也后悔,但嘴上不肯认输:“查什么查?这不明摆着是假的吗?还‘姚班’,我听都没听过!”
就在这时,我那没摔的备用机,一部老年款的诺基亚,尖锐地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张伟”。
我老婆的弟弟,我那个趾高气昂的小舅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
这家伙的儿子跟我家李木同级,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他这时候打电话来,准没好事。
我按下接听键,开了免提。
“喂,姐夫啊!查分了吧?我家张博考了685!全省排名估计能进前三百!清华北大是稳了!你家李木呢?”
张伟那得意洋洋的声音,像一把锥子,隔着电话线就往我耳朵里钻。
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瞥了一眼旁边的李木。
李木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还……还在查,网有点卡。”我含糊其辞。
“卡什么呀!我这都查完了!你快看看!哎呀,李木平时也挺努力的,怎么没听他说起估分啊?我家张博估分680,这还考超常了!”
他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我脸上扇巴掌。
什么叫“也挺努力”?那口气,好像我们家李木能考上个二本都是祖上烧高香了。
“他……他可能没发挥好。”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干涩无比。
“嗨呀,没事儿姐夫!一次考试而已!不行就复读嘛!男孩子,晚一年也没什么!实在不行,我帮你问问,我那朋友公司正好缺个行政助理,一个月四千块,五险一金都有,也算是个出路嘛!”
我“啪”地挂了电话,气得浑身发抖。
他那哪是安慰?那是赤裸裸的羞辱!
我看着李木,他依然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仿佛刚才那通电话跟他毫无关系。
“你听到了吗?”我冲他吼,“你听到了吗!这就是你考288分的结果!你舅舅都给你安排好出路了!行政助理!你满意了?”
“爸,你为什么总要在意别人怎么说?”李木抬起头,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
他的眼神很亮,亮得让我有点心慌。
“我不在意?我能不在意吗?我李建军辛辛苦苦一辈子,图什么?不就图你有点出息,能抬头挺胸做人吗?”
“我现在就不能抬头挺胸做人了吗?”他反问。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是啊,为什么呢?
我做了一辈子装修,跟各种业主、工头、材料商打交道,陪笑脸,受闲气,有时候为了几百块的尾款能磨上一个月。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瞧不起。
我以为,只要儿子学习好,考上名牌大学,我就能在所有人面前扬眉吐气。
可现在……
我看着那张“姚班”的通知,又看了看儿子固执的脸,心里乱成一团麻。
张岚叹了口气,从我手里拿过那张纸,仔细看了起来。
“老公,这上面有联系电话和邮箱,要不……我用我手机查查?”她小声说。
我没吭声,算是默许了。
张岚走到阳台,我隐约听到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好像生怕被人听到。
我看着李木,他已经回到自己房间,又坐到了电脑前,戴上了耳机,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着,屏幕上是我完全看不懂的绿色代码。
那个世界,我不懂。
就像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会对舅舅的炫耀无动于衷。
难道他真的不在乎吗?
过了大概十分钟,张岚回来了,脸色很复杂。
“怎么样?”我赶紧问。
“电话打通了,”她说,“对方说是清华大学招生办的。”
我心里一跳。
“然后呢?他们怎么说?是不是说是骗子?”
“他们说……确实有这个‘姚班’,是招计算机天才的,不完全看高考分数。”张岚的声音有点犹豫。
“那288分呢?”我追问核心问题。
“我没好意思直接问分数,”张岚白了我一眼,“我旁敲侧击地问了问录取流程。他们说,主要是看一个叫‘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成绩,简称NOI。”
“NOI?”又是一个我没听过的词。
“对,他们说,能在那个比赛里拿到金牌,并且通过他们集训营最终面试的,高考只要过一本线就行。”
一本线?我们省今年的一本线是520分。
他这288,离一本线还差着一个珠穆朗玛峰呢!
“那不还是没戏吗!”我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瞬间又被浇灭了。
“你听我说完!”张岚瞪我,“但是,他们说,对于极少数特别顶尖的,比如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可以……可以申请破格录取。”
“破格录取?”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在坐过山车。
“那……那李木他……”
张岚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问他是不是入选了国家集训队,那边老师说涉及学生隐私,不能透露。让我直接问孩子。”
我俩一起望向李木的房门。
那扇门,此刻像是一道分界线,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门前,敲了敲。
“李木,你出来一下。”
他摘下耳机,走了出来。
“你那个……什么NOI,考得怎么样?”我问得有些艰难。
“全国金牌,第一名。”他说。
“……什么?”我和张岚异口同声。
“所以,我入选了IOI国家队,要去打世界赛的。”他补充道,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
IOI,又是一个新名词。
但我听懂了“世界赛”三个字。
“所以……那个288分……”
“哦,那个啊。”李木终于露出了一丝像是“不好意思”的表情,“我没怎么复习文化课,高考前一天晚上还在打一场国外的线上比赛,有点困,语文和英语作文都没写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时间做。”
我:“……”
张岚:“……”
我们夫妻俩,面面相觑,感觉脑子已经彻底不够用了。
一个全国冠军,世界级选手,就坐在我们家沙发上,而我刚刚因为他高考288分,摔了自己的手机,还想给他找个行政助理的工作。
这简直是……年度最佳黑色幽默。
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比刚才被张伟羞辱时还要燙。
“那……那个‘姚班’的最终面试呢?”张岚颤声问。
“通知书上不是写了吗,下周三,去北京。”李木说。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我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但这次的吼声里,愤怒少了, bewildered and frustrated.
“我说了啊。”李木一脸无辜地看着我,“我昨天就跟你说我考得不错,清华应该没问题。你自己不信,还说我做白日梦。”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饭,他确实说过一句“考得还行”,我当时还嗤之以鼻:“你?还行?能上个大专我就烧高香了!”
我瞬间破防了。
原来,眼瞎心盲的,一直是我自己。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着地上那部摔碎的手机,突然觉得它碎的不是屏幕,是我的认知。
我辛辛苦苦做装修,认识的都是工头、设计师、客户,我们谈论的是哪家的瓷砖便宜,哪家的防水做得好,谁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分,谁家又买了新车。
这就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分数”是一把万能钥匙,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直观的标尺。
685分,就是人中龙凤。
288分,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把标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评价体系。
一个我完全陌生,甚至无法理解的体系。
张岚显然比我接受得快,她已经开始兴奋地计划起来。
“去北京?那得赶紧买票啊!还要给你准备衣服!你看看你这身衣服,跟咸菜干似的!”
她一边说,一边冲进李木房间,开始翻箱倒柜。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弹。
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
这反转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我拿起茶几上那张皱巴巴的打印纸,又看了一遍。
“姚班”、“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uin队”。
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就像天书。
我拿出我的老年机,笨拙地用九宫格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姚班”是什么。
搜索结果跳出来的一瞬间,我倒吸一口凉气。
“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由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院士创办,致力于培养领跑国际的顶尖计算机人才。”
“‘姚班’的学生,一半本科毕业后赴世界顶尖高校深造,另一半留在国内读研,毕业后大多进入谷歌、微软、华为等头部企业核心研发部门,或是成为新兴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姚班’的录取难度,甚至高于清华任何一个普通专业的高考分数线。”
我一条一条地往下看,手心开始冒汗。
我那个只会闷头打电脑,连跟亲戚打招呼都脸红的儿子,竟然跟这些“天才”、“领跑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感觉自己像个闯入巨人国的格列佛,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巨大而不真实。
晚上,张岚做了一大桌子菜,庆祝。
她把家里那瓶我珍藏了好几年,准备等李木考上大学才喝的茅台都拿了出来。
饭桌上,张岚一个劲地给李木夹菜,嘴都合不拢。
“儿子,多吃点,看你瘦的!去北京面试,可得精神点!”
我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闷下去,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爸,少喝点。”李木看了我一眼。
“没事。”我摆摆手,又倒了一杯。
我不是不高兴,我是……五味杂陈。
有种巨大的、不真实感包裹着我。
我看着对面的儿子,他还是那个样子,吃饭安安静静,话不多。
可在我眼里,他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我庇护,需要我为他规划未来的孩子了。
他已经在他自己的那条赛道上,跑出了很远很远,远到我连他的背影都快看不清了。
而我这个当爹的,不仅没给他加过油,甚至还在他身后拼命地想把他拽回我熟悉的、我认为“正确”的跑道上。
我真是个混蛋。
“对不起,儿子。”我端起酒杯,“之前是爸不对,爸……眼界窄了。”
李木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没事,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他举起面前的橙汁,跟我碰了一下杯。
我眼眶一热,赶紧又喝了一口酒,把那股酸涩压下去。
男人嘛,不能在儿子面前掉眼泪。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了手机店。
“老板,修个屏幕多少钱?”我把我的“尸体”递过去。
老板看了看:“你这……原装屏得一千二。”
“这么贵?”我肉疼了一下。
“你这是旗舰机啊大哥,屏幕本来就贵。要不给你换个国产屏?六百。”
我想了想李木那张平静的脸,咬了咬牙。
“换原装的。”
我不能让儿子觉得,他爸是个连手机都修不起的失败者。
虽然,在认知上,我确实是个失败者。
等待修手机的时候,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建军啊,木木成绩出来没?你弟(我哥)家那丫头,考了620,说要去上海读大学了!你家木木怎么样啊?”
我哥是中学老师,他女儿从小就是学霸。
往年,我最怕接这种电话。
但今天,我腰杆子莫名地硬了起来。
“妈,李木考得……挺特殊的。”我斟酌着用词。
“特殊?啥意思?好还是不好啊?”
“挺好的,被清华预录取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云淡风轻,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d秒。
“啥?清华?建军你没睡醒吧?就李木那成天打游戏的样儿?”
我妈的反应,跟我初听时一模一样。
看来,这事儿在普通人听来,确实跟天方夜譚差不多。
我耐着性子,把我昨天刚学到的那些词——“姚班”、“奥赛金牌”、“国家队”,笨拙地解释了一遍。
我妈听得云里雾里,最后总结了一句:“反正就是说,咱家木木要上清华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哎哟我的老天爷啊!祖坟冒青烟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激动得都快哭了,“我得赶紧去告诉你爸!你等着,我让你爸跟你说!”
很快,电话里传来我爸那洪亮又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
“建军,是真的吗?”
“爸,是真的。”
“好!好!好!”我爸连说了三个“好”字,“不愧是我李家的孙子!有出息!你告诉木木,回来爷爷给他包个大红包!”
挂了电话,我心里那点虚浮的 pride 才终于落到了实处。
父母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
手机修好了,屏幕光洁如新。
我付了钱,心里那点肉疼也被喜悦冲淡了。
回到家,我看到张岚正在给李木收拾行李。
“这件T恤太旧了,扔了!这件,图案太幼稚了!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她把我前年给她买的那件羊绒衫都翻了出来,往李木身上比划。
“妈,这是女式的。”李木一脸无奈。
“什么女式男式的,暖和就行!北京早晚温差大!”
我看着这 comical 的一幕,忍不住笑了。
这是我这几天来,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我走过去,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塞到张岚手里。
“干嘛?”张岚愣了。
“去,给儿子买几身体面的衣服。从里到外,全换新的。”我说,“别怕花钱。”
我做装修的,平时对钱看得很紧,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心甘情愿地“挥霍”。
张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木,眼睛红了。
“你这老东西,总算开窍了。”她捶了我一下。
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市里最高档的商场。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闊綽过。
给李木买了两套休闲装,一套运动装,一双名牌运动鞋,还有一个新书包。
结账的时候,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刷卡机吐出小票的声音,我觉得比工地上打桩机还好听。
李木换上新衣服,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虽然还是有点瘦,但眉宇间那股自信,是怎么也藏不住的。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儿子,好像还挺帅的。
周二晚上,我们送李木去火車站。
我们买了卧铺票,张岚给他带了吃的喝的,还有一路上的换洗衣物,塞了满满一个旅行箱。
临上车前,张岚还在不停地嘱咐。
“到了北京安顿好了就给家里来个电话。”
“面试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
“钱够不够?我再给你转点?”
李木一直点头:“知道了妈,够了。”
我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千言万語,到了嘴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加油”?他已经足够优秀了。
说“别紧张”?他心理素质比我还好。
检票的广播响了。
李木跟我们挥了挥手,准备进站。
“儿子。”我突然叫住他。
他回过头。
我走上前,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爸为你骄傲。”我拍了拍他的背,声音有点哑。
李木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他轻轻地回抱了我。
“谢谢爸。”
我松开他,看到他眼圈也有点红。
这小子,原来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他转身,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跟张岚一直站在那儿,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回家的路上,张岚一直在抹眼泪。
“你说,儿子一个人在北京,能习惯吗?”
“他都多大了,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空落落的。
感觉像是养了十几年的鹰,终于展翅飞向了天空,既欣慰,又失落。
第二天,也就是李木面试那天,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工地上,我指挥工人铺地砖,铺着铺着就走神了。
“李老板!歪了!歪了!”一个工人喊我。
我回过神,看到一排地砖铺得歪歪扭扭,像一条蛇。
我赶紧让人撬了重铺,心里烦躁得不行。
下午,我干脆请了假,提前回了家。
张岚也一样,坐立不安,一会儿擦擦桌子,一会儿拖拖地,眼睛时不时就瞟向手机。
我们在等李木的电话。
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无比漫长。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每一下都敲在我心上。
晚饭我们也没心思做,点了份外卖。
外卖超时了半小时,我竟然一点都没生气,连申请超时赔付都忘了。
终于,晚上八点多,手机响了。
是李木。
张岚一把抢过手机,按了免提。
“喂!儿子!怎么样?面试顺利吗?”
“嗯,还行。”李木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累。
“什么叫还行啊?过了还是没过啊?”我急得凑过去问。
“过了。”他说,“老师跟我说,手续办完,九月份直接来报到就行。”
“真的?!”张 a and I shouted in unison.
“嗯。”
“太好了!太好了!”张岚喜极而泣。
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能一个劲地拍大腿。
那块被我摔碎的手机屏幕,那1200块钱,花得太值了。
就在我们激动万分的时候,我的老年机又不知好歹地响了。
还是张伟。
我看了张岚一眼,她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示意我接。
我清了清嗓子,接了电话。
“喂,姐夫,考虑得怎么样了?我那朋友公司催我了,那行政助理的岗位可是个香饽饽,好几个人抢呢!你要是再不决定,可就没了啊!”
张伟的语气里,充满了“我为你操碎了心”的优越感。
我笑了。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扬眉吐气的笑。
“张伟啊,谢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李木那工作,恐怕是去不了了。”
“怎么?嫌钱少?哎呀姐夫,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四千块就不错了!不能好高骛远啊!”
“不是钱的事儿。”我说,“他九月份要去清华报到了,没时间上班。”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比上次我妈那次还要久。
久到我甚至能想象出张伟那边,嘴巴张成O型的滑稽样子。
“清……清华?”张伟的声音都变调了,“姐夫,你没开玩笑吧?李木不是才考了……我听说才两百多分?”
消息传得还真快。
“是啊,288分。”我坦然承认,“不过,他是被‘姚班’录取的,走的不是寻常路。”
我故意把“姚班”两个字咬得很重。
“姚班……”张伟在电话那头喃喃自语,显然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去查的。
这就够了。
“行了,不跟你多说了,我们一家人正庆祝呢。你家张博也恭喜了,685分,真厉害。”
我主动挂了电话。
那一刻的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三伏天喝了一大瓶冰镇汽水,从头爽到脚。
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争一口气。
为我自己,也为我儿子。
挂了电话,我看到张岚和电话那头的李木都在笑。
“爸,你有点帅啊。”李木在电话里说。
我老脸一红:“臭小子,跟你爸还贫。”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
这半辈子的委屈、憋屈、不甘,仿佛都在这一天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家成了亲戚朋友间的“传奇”。
288分上清華的故事,版本越傳越神。
有的说李木是黑客,把清华的系统给黑了,人家没办法才录的他。
有的说李木发明了什么了不得的软件,被国家看中了。
还有的说,我家祖坟风水好,出了个文曲星。
我每次听到这些,都只是笑笑,不解释。
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我解释了也没用。
就像我以前,也无法理解李木的世界一样。
八月底,我们陪李木去北京报到。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踏进清华的校园。
校园很大,绿树成荫,到处都是骑着自行车的年轻面孔。
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和朝气,那是属于知识和未来的光芒。
我看着身边同样年轻的儿子,心里感慨万千。
原来,通往这里的路,不止一条。
我们帮他把宿舍安顿好。
宿舍是四人间,另外三个室友也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天才少年”。
他们聊的话题,我一句也听不懂。
什么“分布式计算”、“神经网络”、“底层逻辑”。
我感觉自己像个文盲。
我悄悄把李木拉到一边,又塞给他两千块钱。
“爸,我钱够用。”他推辞。
“拿着!”我把钱硬塞进他口袋,“这是爸给你的底气。在外面,别委屈自己。”
我知道,这点钱在北京不算什么。
但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安顿好一切,我和张岚准备离开。
在校门口,我们又一次拥抱。
“儿子,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
“嗯,爸,妈,你们也保重身体。”
看着他转身走进那座著名的“二校门”,我突然意识到,他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与我们截然不同。
他会飞得很高,很高。
高到我只能在地面上,仰望着他。
回去的火车上,张岚又哭了。
“这孩子,以后一年也就回来两次了。”
我拍了拍她的手,没说话。
我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但更多的是一种踏实的,满足的骄傲。
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装修生意,不好也不坏。
张岚每天还是会去社区跳广场舞,偶尔抱怨一下社区团购的冷链不给力。
我们学会了用微信跟儿子视频。
每次视频,他都在图书馆或者实验室。
背景里总是匆匆而过的身影,和各种我看不懂的仪器设备。
他话不多,总是说“挺好的”、“别担心”。
我知道,他不是敷衍。
他的世界,节奏太快,他没有时间说太多废话。
有一次,我跟他视频,他正在吃一份外卖。
“怎么又吃外賣?對身體不好。”我忍不住嘮叨。
“爸,沒事,一個算法推到一半,沒時間去食堂。”他扒拉了兩口飯,又把目光投向了旁邊的電腦屏幕。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像一群蚂蚁。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突然覺得,我以前对他的所有要求——要懂事,要会来事,要成绩好,都显得那么渺because of him.
他不需要活成我期望的样子。
他只需要做他自己。
而他自己,已经比我期望的,要好上一万倍。
过年的时候,张伟带着他儿子张博来拜年。
张博在北大读金融,一身名牌,谈吐间都是“资本”、“市场”、“风口”。
张伟一脸得意,不停地问我:“姐夫,李木怎么样啊?在清华还习惯吧?他们那专业,毕业了好找工作吗?不像我们金融,出来都是去投行的。”
我笑了笑,给他倒了杯茶。
“还行吧,前两天刚拿了个什么奖,学校奖励了十万块钱。”
“什么奖?”张伟追问。
“我也记不清了,好像叫什么……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的金牌吧。”我轻描淡写地说。
我看到张伟端着茶杯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他儿子张博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和敬佩的神情。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来自攀比和炫耀。
而是来自,我终于真正理解并认可了我儿子的价值。
我不再需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他。
因为他本身,就在定义一种新的标准。
那天晚上,我给李木发了条微信。
“儿子,你舅舅今天来了,我帮你‘装’了个X。”
过了很久,他回了我三个字。
“爸,牛。”
后面跟了个“”的表情。
我看着那三个字,乐得在床上打了好几个滚。
张岚骂我:“多大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我就是高兴。
我高兴的不是我赢了谁。
而是我终于和我那个曾经“无法理喻”的儿子,站在了同一个阵地。
我们成了战友。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李木就大四了。
他没有选择出国,也没有选择读研,而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了个公司。
公司做的项目,我听不懂,大概是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有关。
创业很辛苦。
他有一次视频,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
张岚心疼得直掉眼 tear.
“儿子,要不别干了,咱找个安稳的工作吧,去华为,去阿里,不都挺好的吗?”
“妈,没事,我喜欢现在做的事。”他笑着说,但掩不住满脸的疲惫。
我看着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自己刚开始包工程的时候。
也是这样,没日没夜,吃住都在工地上,为了一个项目,能几天不合眼。
我没说话,默默地给他转了二十万块钱。
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
“爸,你干嘛?我不要!”他立刻发微信过来说。
“拿着。”我回他,“这不是给你的,是爸投资你的。以后公司赚钱了,记得给老爸分红。”
我知道,这二十万对他公司的估值来说,可能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但这是我的态度。
爸不懂你的代码,但爸支持你的梦想。
又过了一年,春节。
李木回来了。
开着一辆我叫不上名字的电动汽车,安静地停在楼下。
他看起来成熟了很多,不再是那个瘦削的少年了。
他给我和张岚带了很多礼物,都是他托人从国外买的。
他告诉我,他的公司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级别的融资。
他还告诉我,他把当年我“投资”的那二十万,翻了一百倍,打到了我的卡上。
我查了查银行卡余额,看着那一长串的零,手都在抖。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儿子,这……这太多了……”
“不多,爸。”他说,“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当初摔的那个手机,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那天你摔了手机,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么失控,那么失望。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做出点名堂来,让你为我骄傲。”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流了下来。
原来,我那个混蛋一样的举动,竟然成了他前进的动力。
命运这东西,真是奇妙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又坐在一起吃饭。
还是那张旧饭桌,还是那些家常菜。
但一切,又都好像不一样了。
我看着身边这个已经比我高,比我 successful, 比我更懂这个世界的儿子。
心里那点因为“被超越”而产生的失落,早已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源于血脉的,深沉而厚重的自豪。
养儿子就像开盲盒,开到最后才知道,你以为的废铁,其实是块纯金。
本文标题:男童拿现金买手机被老板哄吓拒售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14097.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