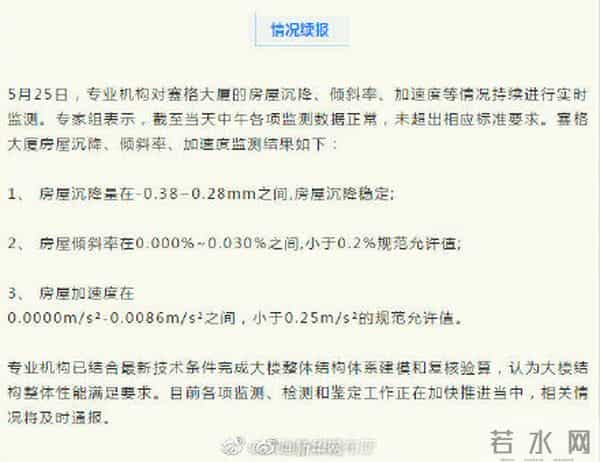5岁女童去上海探亲 3天走丢3次
隔着电话,我听见女儿安娜在那头哭了,她说,妈妈,他们不让我上飞机,我的健康码一直是红色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彻底失去她了——至少在今年春节,是这样。
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整整半年。她在美国的大学一放假,我就开始计算隔离期,提前三个月刷着天价机票,把家里她那个小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换上了她最喜欢的淡蓝色床单。我甚至提前跟单位请好了年假,就为了能完完整整地陪她过一个地道的中国年,吃外婆做的酱菜,看一场真正的庙会。
我总想着,要把她身上那份越来越淡的中国味,再重新找补回来。我以为我能做到,我以为只要我努力,血缘和亲情就能跨越那本蓝色的护照。
然而,一切的崩塌,是从浦东机场T2航站楼那个冰冷的玻璃柜台开始的。
第1章 被拒绝的家门
“对不起,女士,您女儿是外国国籍,根据最新的防疫政策,我们无法为她办理登机手续。”
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地勤人员,声音隔着一层口罩和玻璃,显得有些沉闷和失真,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进我的耳膜。
我攥着手里的两本护照,一本是我的暗红色中国护照,一本是安娜的深蓝色美国护照。那蓝色,在机场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不可能,”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努力想挤出一个平和的微笑,但嘴角却不听使唤地抽动着,“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核酸检测报告、使馆的证明……所有的,你看,都在这里。”
我把一沓厚厚的文件往前推了推,纸张的边缘因为我反复的检查和整理,已经有些卷曲。那是我过去几个月里所有心血的证明。每一份文件,都代表着无数个夜晚的邮件往来和提心吊胆的等待。
地勤人员礼貌地摇了摇头,他甚至没有伸手去接那沓文件。“林女士,政策是昨天深夜刚刚更新的。我们也是早上才接到通知。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规定就是规定。”
“规定?”我感觉自己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顶,“什么规定能让一个女儿回不了妈妈的家?她爸爸是美国人,可我是她妈,我是中国人啊!她外公外婆都在上海,这里就是她的家!”
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引来了周围一些旅客的侧目。他们脸上带着同情、好奇,或许还有一丝庆幸。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打乱所有人的行程。
安娜站在我身后,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她今年十九岁,个子已经比我高了小半个头,一头栗色的长发,五官是东西方恰到好处的融合,但那双眼睛,是我的,深棕色的,此刻正盛满了不安和委屈。
她用还算流利的中文小声说:“妈妈,别激动,我们再问问。”
看着女儿故作坚强的样子,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我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焦躁和愤怒压下去,重新换上恳求的语气:“同志,求求你,你再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通道?人道主义……我们愿意多隔离一段时间,多久都可以。她还是个学生,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
地勤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无奈,他拿起对讲机,低声和另一头沟通了几句。那几分钟,我感觉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我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能感觉到安娜在我身后越攥越紧的手。
最终,他对我们摇了摇头,那动作缓慢而决绝。
“真的没办法,林女士。您是中国公民,可以登机。但您的女儿……我们没有权限。”
我,可以登机。
我的女儿,不行。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我们母女俩,被一本护照的颜色,硬生生地隔绝在了同一个机场的两个世界里。我可以回家,而我的女儿,我的心头肉,却被挡在了家门之外。
安娜的眼圈红了。她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一步,似乎想和我之间拉开一点距离,仿佛这样就能让这荒诞的一幕显得不那么残忍。
“那我……不回去了。”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嘶哑。
“妈妈!”安娜急了,“你胡说什么?外公外婆还在家等你。你回你的家,我……我再想办法。”
她说的“你的家”,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细微的差别,让我的心又是一痛。我知道她不是有意的,但在这一刻,这个词精准地概括了我们尴尬的处境。这里是我的国,我的家,却不是她的。
机场的广播在催促着旅客登机,开始涌向登机口。我和安娜被滞留在原地,像两座孤岛。周围的世界依旧在运转,别人的归途仍在继续,只有我们的路,在这里被硬生生斩断了。
我看着女儿那张写满无助的脸,十九岁的年纪,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她从出生就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来回回,中文是磕磕绊绊学会的,筷子是用得歪歪扭扭的。我一直努力想让她明白,无论她拿着哪国护照,上海这里,有外公外婆,有妈妈,就是她永远的根。
可现在,这根,被政策,被这本蓝色的护照,轻易地否定了。
最终,我没有登上那架飞机。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异国他乡的机场。我们退了票,拖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像两个打了败仗的士兵,离开了那个充满希望又带来绝望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家机场附近的酒店住下。房间里有两张床,安娜躺在一张上,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我知道她在哭,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任何语言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打开手机,开始疯狂地查询各种信息,拨打各种热线电话。大使馆的、航空公司的、出入境管理局的……电话那头永远是忙音,或者是礼貌却冰冷的官方回复。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但目前没有新的政策。”
“建议您关注官方网站的通知。”
“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
夜深了,窗外是飞机起起落落的轰鸣声。每一声,都像是在提醒我,有无数的人正在回家,而我的女儿,回不了家。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和安娜的爸爸大卫办理离婚手续时的情景。那时安娜才五岁,对于国籍的选择,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大卫坚持要安娜保留美国国籍,他说那能给她更好的教育和未来。而我,虽然心里万般不舍,但也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或许对她的人生是“更优选”。
我天真地以为,一纸国籍,不过是个身份符号,改变不了我们是母女的事实。只要我爱她,只要我常带她回来,她就不会忘记自己的另一半血脉。
我甚至还记得,当时我对犹豫不决的父母打包票说:“爸,妈,你们放心。国籍算什么?她身体里流着我们林家的血,我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咱们的家门,永远对她开着。”
现在想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家门,就在那里,隔着一片海,却像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宇宙。
我扭头看了看安拿,她似乎已经睡着了,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走过去,轻轻替她掖了掖被子。她的睡颜,还带着孩子气的纯真。
我的女儿,我该拿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第2章 空荡荡的房间
在机场酒店待了两天,我们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结果都一样:此路不通。
政策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我们找不到任何缝隙。安娜的情绪从最初的委屈变成了沉默的沮pad,她大部分时间都戴着耳机,看美剧或者听音乐,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消化自己的失望,也是在避免和我讨论那个我们谁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了我妈赵桂芬的电话。
“秀英啊,你们怎么还没到啊?不是说昨天就该到了吗?我跟你爸,酱菜都给你女儿腌好了,她最爱吃的那个咸笃鲜,火腿都炖烂了。”
我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我走到阳台上,关上玻璃门,才敢开口。
“妈,我们……我们回不来了。”
“什么叫回不来啦?”我妈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飞机晚点啦?晚到什么时候?你跟安娜说,外婆给她留着好吃的呢。”
“不是晚点,”我艰难地组织着语言,“安娜她……因为是美国护照,上不了飞机。政策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甚至能想象到我妈脸上的表情,从兴奋到错愕,再到难以置信。
过了好一会儿,我爸林建国的声音传了过来,低沉而严肃:“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我把机场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每说一个字,都感觉像是在揭自己的伤疤。我说得口干舌燥,说到最后,声音都带了哭腔。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机场这边,走不了。”
“胡闹!”我爸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什么叫走不了?你是中国公民,你先回来啊!把孩子一个人扔在那像什么话?……不对,她一个外国人,你跟着耗在那干嘛?她多大了?十九了!不是三岁小孩!”
我爸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讲原则,也有些固执。在他的世界里,事情总该有个条理,有规矩。而眼下我们母女的处境,显然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爸,我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我感到一阵无力,“她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
“那当初是谁非要让她入那个美国籍的?”我爸的声音陡然拔高,这句话像一把淬了火的刀子,精准地捅在我最痛的地方,“我早就说过,中国人,就该有中国根!你看看现在,弄成什么样子了?家就在眼前,回不来!这叫什么事!”
“建国!你少说两句!”我妈在那头抢白了一句,然后声音又转向我,带着哭音,“秀英啊,你别听你爸的,他也是急的。那……那现在怎么办啊?我可怜的外孙女……”
听着电话里父母焦急又带着责备的声音,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捂着嘴,不想让他们听到我的哭声。
是啊,当初是我做的决定。是我以为自己能为女儿规划一个“更好”的未来,是我天真地以为血缘可以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所有的后果,都该由我来承担。
挂了电话,我靠在冰冷的玻璃门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酒店房间的空调开得很足,但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回到房间,安娜已经坐了起来,她显然听到了我刚才的通话。
“外公是不是生气了?”她小声问,眼神里带着一丝愧疚。
我摇摇头,走过去坐在她床边,勉强笑了笑:“没有,外公是担心你。”
“Mom,” 安娜换回了她更习惯的英语,“Maybe… maybe you should go back first. I can go back to my dorm in the US. It’s okay, really.”
她越是表现得懂事,我心里就越是难受。回美国的宿舍?现在是假期,宿舍空无一人,冷冷清清。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一切?我做不到。
“别说傻话了,”我摸了摸她的头,“妈妈不会丢下你的。我们再想想办法。”
可“办法”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又去哪里找呢?
当天下午,我们接到了航空公司的正式通知,由于短期内政策不会改变,建议我们办理全额退票。这基本上是宣告了我们这次回国计划的彻底失败。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退票确认信息,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破灭了。
“安娜,”我转头看着她,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我们……回不去了。你回美国,我送你去机场。”
安娜愣住了,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放弃。
“Mom…”
“听话,”我打断她,“你先回学校,至少那里是熟悉的环境。我会想办法,等政策松动了,我立刻给你买票。或者,我去看你。”
这话说得我自己都没底。去看她?我的签证、工作,所有的一切都在国内,哪是说走就走的。
安娜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们重新买了去美国的机票。这一次,手续异常顺利。看着她拿着那本蓝色护照畅通无阻地办理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我心里五味杂陈。这本护照,是她通往世界的门票,却也是隔断她回到外婆家的那堵墙。
在安检口,我们拥抱告别。我能感觉到她纤瘦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照顾好自己,”我一遍遍地叮嘱,“到那边给我报平安,每天都要视频。钱不够了就跟妈妈说……”
“I know, Mom.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too.” 她在我耳边轻声说,“And… say sorry to grandpa for me.”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的人群中,感觉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被硬生生地抽走了。
我没有立刻离开机场,而是一个人拖着那个为她准备的、装满了新衣服和零食的行李箱,回到了上海的家。
打开家门,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玄关处,还放着我为安娜准备的新拖鞋。客厅的茶几上,摆着我妈送来的一大罐酱菜,玻璃罐上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我妈的字:“给安娜,少吃点,咸。”
我走到安娜的房间。淡蓝色的墙壁,崭新的床单,书桌上还放着我特意买来的一束百合花。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里的一切都那么温暖、明亮,充满了迎接主人的喜悦。
可它的主人,却在万里之外。
我把那个沉重的行李箱放在房间中央,没有打开。然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冰冷的墙壁,看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终于放声大哭。
这个我精心布置的、充满爱的空间,此刻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嘲笑着我的无能和天真。
我以为我能给她一个家,可我连家门都没能让她进来。
第3章 太平洋上的电话
安娜回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她几乎每天都要视频通话两三次。
倒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就是想看看她。早晨她起床,我会叮嘱她记得吃早饭;中午她从图书馆出来,我会问她功课累不累;晚上她回到宿舍,我们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很久,直到她困得睁不开眼。
太平洋隔开了我们,网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我贪婪地看着屏幕里女儿的脸,想从她的每一个表情里,确认她一切都好。
她确实表现得很好。一个人去了超市,把空荡荡的冰箱填满;自己研究菜谱,学着做简单的三明治和意面;甚至还把宿舍打扫得井井有条,拍了照片发给我看。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酸楚。我知道,我的女儿正在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被动地加速成长。这种成长,本不该是在这样孤独和无奈的处境下发生的。
这天晚上,视频接通时,安娜那边似乎有些不对劲。她没在宿舍,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在一个公共场所。
“安娜,你在哪儿呢?”我问。
“哦,Mom,我在……在朋友家。”她眼神有些闪躲,摄像头也晃了一下,我瞥见背景像是一个餐厅的后厨。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哪个朋友?我认识吗?大晚上的,你别在外面乱跑。”
“哎呀,你放心啦。”她把镜头转向自己的脸,冲我做了个鬼脸,“就是同学,我们一起做个课题。不说了啊,我这边有点忙,先挂了!”
没等我再问,视频就被匆匆挂断了。
我盯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一种强烈的不安攫住了我。安娜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她刚才的样子,明显是在隐瞒什么。
我立刻想到了她的父亲,我的前夫,大卫·克拉克。
我和大卫已经很多年没有直接联系了。自从离婚后,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就是安娜。他会定期支付抚养费,安娜放假回美国时,他也会去看看她。但除此之外,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他后来再婚,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生活在另一个城市。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从手机通讯录的最深处,翻出了那个几乎被我遗忘的号码。
拨过去的时候,我的手心都在冒汗。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大卫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一点刚睡醒的沙哑:“Hello”
“David, it’s me, Xiuying.” 我开门见山。
那边沉默了几秒,似乎在辨认我的声音。“Oh, Xiuying. What’s up Is Anna okay” 他第一时间问到了女儿,这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
“She’s okay, but… I need to ask you something.” 我把安娜回国被拒,又一个人返回美国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Oh, damn. I heard about the new policy. That’s tough.” 大卫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客气,“So she’s back at the dorm now”
“Yes. But I’m worried about her.” 我把我刚才视频通话的疑虑告诉了他,“David, she’s your daughter too. Can you… can you please go see her Or at least give her a call and find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 I’m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在这一刻,我不得不放下所有的骄傲和过往的恩怨。为了女儿,我只能求助于这个我曾经最熟悉也最想远离的男人。
大卫在那头叹了口气。“Xiuying, you know my situation. My wife is pregnant, and my company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Anna’s university is a fivehour drive from here. It’s not that I don’t want to go, but it’s really difficult for me to get away right now.”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能理解,他有他的新生活,他的难处。可安娜呢?安娜也是他的女儿啊。
“Five hours drive is too long for you” 我的声音冷了下来,“David, do you know how long the flight is from Shanghai to her It’s fourteen hours! And I can’t even get on that plane!”
“Hey, don’t get emotional.” 他的声音也变得有些不耐烦,“I’m just stating the facts. Anna is an adult. She’s nineteen, not nine. She needs to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You can’t protect her forever. This might be a good thing for her.”
“A good thing”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把女儿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却说这是一种“锻炼”。
“是的,一件好事。”大卫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总是太紧张她了,秀英。你让她学中文,学用筷子,带她回中国过年……你总是想把她变成一个中国人。但你必须接受现实,她是在美国长大的,她是个美国人。她需要学会用美国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有事就哭着找妈妈。”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指责我过去十几年的教育方式。我一直以为,让安娜了解并热爱她的中国血统,是我作为母亲的责任。但在大卫看来,这反而成了她不够“独立”的根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不会做,是吗?”我绝望地问。
“I will call her.” 大卫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重了,“I’ll transfer some money to her account. But you need to relax, Xiuying. She’ll be fine.”
我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挂了电话。
窗外的夜色浓重如墨。我忽然觉得无比的孤独和疲惫。
原来,在照顾女儿这件事上,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人。
我以为我们是父母,是同盟。但在现实面前,他首先是他的新家庭的丈夫,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才是我女儿的、那个远在五小时车程之外的父亲。
我点开和安娜的聊天框,看着她的头像——一张她对着镜头笑得灿烂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上海外滩的夜景。那还是前年夏天,我带她回来时拍的。
我忽然意识到,大卫说对了一件事。
我或许,真的该学着放手了。不是放弃她,而是改变我爱她的方式。我不能再把她当成一个需要时刻被保护的小女孩。她被那本护照、被那条国境线,硬生生地推向了独立。
而我这个母亲,能做的,或许不是替她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教会她如何自己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我给安娜发了一条信息:
“宝贝,如果遇到困难,一定要告诉妈妈。但无论发生什么,妈妈都相信你有能力处理好。你是最棒的。”
发完这条信息,我删掉了大卫的电话号码。这一次,是彻底的。
第4章 屏幕里的红烧肉
自从和大卫那次通话之后,我刻意减少了和安娜视频的频率。不再是事无巨细地一天三问,而是变成每天晚上睡前固定半小时的聊天。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盘问她在哪、干了什么的冲动,转而和她聊些轻松的话题。聊她看的电影,聊学校里的趣闻,聊我单位里发生的琐事。我开始学着像朋友一样和她交流,而不是一个焦虑的、控制欲过强的母亲。
安娜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不再是简单的“嗯”、“还好”。她会跟我抱怨某个教授的口音太重,会兴奋地跟我分享她新淘到的二手书。
那天晚上,我们照例视频。她那边看起来精神不错,但脸颊好像瘦了些。
“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我还是没忍住,露出了老母亲的本色。
“哪有,”她笑着反驳,“我今天还自己做了顿大餐呢。”
“是吗?做的什么?”我来了兴趣。
她把摄像头转过去,对准了书桌上的一盘东西。盘子里是几块颜色看起来黑乎乎、奇形怪状的肉块,旁边还有一碗白米饭。
“红烧肉!”她得意地宣布。
我看着那盘“红烧肉”,差点笑出声。那哪里是红烧肉,分明就是一盘酱油炖肉块,颜色深得发苦,汤汁也收得太干了。
“怎么样,看起来还不错吧?”她期待地问。
“嗯……非常有创意。”我憋着笑,用了一个委婉的词。
“我就是照着网上的菜谱做的,但是味道好奇怪。”她用叉子戳起一块,放进嘴里,皱着眉头说,“又咸又硬,一点也不像外婆做的。”
听到“外婆”两个字,我的心又被轻轻刺了一下。
“傻孩子,”我柔声说,“红烧肉哪是那么好做的。要炒糖色,要放料酒、生姜、八角……火候最重要,要用小火慢慢炖,才能把肉里的油逼出来,炖得软糯入味。”
我一边说,一边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我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那熟悉的酱油和冰糖的香气,是我从小到大最深刻的味觉记忆。
“这么复杂啊……”安娜吐了吐舌头,“我以为只要酱油和肉就行了。”
“下次,妈妈教你。”我脱口而出。
“怎么教?你又不在。”她随口一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失落。
我看着屏幕里她的脸,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
“我们……可以在线教啊。”我说,“明天你去超市,把材料买好。我在这边,和你一起做。我做一步,你跟着做一步,怎么样?”
安娜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吗?可以吗?那太酷了!”
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跨越太平洋的“厨艺教学”。
我把手机用支架固定在厨房的台面上,摄像头对准我的灶台。安娜则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宿舍简陋的厨房里。
“好了,第一步,五花肉切块,冷水下锅,放两片姜,几粒花椒,开火焯水。”我一边操作,一边详细讲解。
屏幕那头,安娜手忙脚乱地模仿着。她的刀工很差,肉块切得大小不一。焯水的时候,把水溅得到处都是。
“别急,慢慢来。”我耐心地指导她。
炒糖色是关键的一步。我让她把火调到最小,看着锅里的冰糖从大块融化成液体,再慢慢变成焦糖色,冒起细密的小泡。
“就是现在!快,把肉倒进去!”我大声提醒。
安娜“啊”地叫了一声,慌乱地把一盆肉倒进锅里,油花四溅,吓得她往后跳了一步。
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小意外,但我们俩都乐在其中。厨房里充满了我们的笑声和对话声,我感觉她好像就在我身边,我们就像从前一样,在家里一起准备晚餐。
一个多小时后,两锅红烧肉同时出炉。
我这边的,色泽红亮,香气扑鼻。
安娜那边的,虽然样子还是有些“惨不忍睹”,但比起昨天那盘“黑炭”,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吹了吹,放进嘴里。
她咀嚼的动作慢慢停了下来,然后,眼睛一点点地红了。
“妈妈,”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我……我好像吃到了外婆家的味道。”
那一刻,我隔着屏幕,看着泪流满面的女儿,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忽然明白了。
我无法穿越太平洋去照顾她的生活,但我可以把“家”的味道,通过这根网线,传递给她。
从那以后,“在线厨房”成了我们母女俩的固定节目。
我教她做西红柿炒蛋、可乐鸡翅、青椒肉丝……都是些最简单的家常菜。我们不再过多地谈论回国的事,不再抱怨那些无能为力的政策。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柴米油盐,围绕着一蔬一饭。
我发现,安娜变得开朗了很多。她开始在朋友圈里晒自己做的菜,虽然还是经常“翻车”,但她会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分享自己的失败品。她的同学们都觉得她很酷,一个会做中国菜的美国女孩。
有一次,我爸妈也加入了我们的视频。他们看着屏幕里那个系着围裙,正在认真切土豆丝的外孙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爸对着手机,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大声说:“Anna, good job! Potato, cut thin, very good!”
安娜在那头笑得前仰后合。
我看着这幅温馨又有些奇特的画面,心里百感交集。
一本护照,一道国境线,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和痛苦。但它,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连接。
我们无法在物理空间上团聚,却在味觉和记忆里,重建了家的感觉。
那个曾经让我感到绝望和无助的难题,似乎正在被一盘盘屏幕里的红烧肉,慢慢地消解。
我开始明白,家,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一种国籍身份。它更是一种味道,一种习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割舍的牵挂。
第5章 迟来的真相
“在线厨房”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春节。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和女儿一起过年。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围在桌前吃年夜饭,桌上摆满了菜,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特意在安娜的座位上,也摆了一副碗筷。
我们和安娜约好了时间,等她那边天亮了,就视频连线,一起“云过年”。
吃完饭,我爸把我拉到阳台。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说:“这个,给安娜的。”
我接过来,红包很沉。
“爸,她人都不在……”
“不在也得给,”我爸打断我,他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叹了口气,“秀英,前段时间……是爸说话太重了。爸就是……就是心疼孩子。”
“我知道。”我鼻子一酸。
“你一个人,把她拉扯这么大,不容易。”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国籍的事,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只要孩子好好的,比什么都强。你看她现在,不是也挺独立的嘛,还会做饭了。”
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这几句话,已经是他能说出的最柔软的话了。我知道,我们家因为这件事产生的裂痕,正在慢慢愈合。
和安娜的视频电话,是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接通的。
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卫衣,特意画了淡妆,看起来喜气洋洋。
“外公外婆,妈妈,新年好!恭喜发财!”她用字正腔圆的中文给我们拜年。
我爸妈笑得合不拢嘴,对着屏幕一个劲儿地说:“好,好,我们安娜也好!”
我们聊了很久,给她看了家里的年夜饭,看了窗外的烟花。她也给我们看了她宿舍窗外的雪景。她说,她给自己下了一碗速冻水饺,算是过了年。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那么正常。
直到视频快结束时,她忽然说:“Mom,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其实……没有住在宿舍。”她说。
我愣住了。
“那你住在哪?”
“我……我在一家中餐馆打工,包吃住。”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那天你看到我视频的背景,就是餐馆的后厨。我怕你担心,所以撒了谎。”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打工?餐馆?后厨?
这些词汇,和我那个在象牙塔里读书的女儿,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
“你为什么要去打工?我给你的钱不够吗?”我急切地问,声音都在发抖。
“够的,妈妈,你的钱我一分都没动。”安娜摇了摇头,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超乎年龄的平静和坚定,“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花你的钱了。你为了我回来,退了机票,在机场酒店住了那么久,肯定花了不少钱。而且……我想自己挣钱,买一张回家的机票。”
买一张回家的机票。
这句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我的心上。
“你……你都做什么工作?”我艰难地问。
“洗碗,择菜,有时候也帮忙端端盘子。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中国人,人很好,很照顾我。”她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可我无法想象那个画面。我的女儿,那个从小连碗都没洗过的孩子,在餐馆油腻的后厨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重复着机械的劳动。她的那双手,是用来弹钢琴、画画的,不是用来泡在冰冷的洗碗水里的。
“安娜……”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Mom, don't cry.” 她在屏幕那头,反而安慰起我来,“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辛苦。而且,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了赚钱有多不容易,也学会了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我的厨艺进步神速,老板娘亲自教我做锅包肉呢!”
我看着她故作轻松的笑脸,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现实。我以为,我用“在线厨房”的方式,很好地安抚了她的情绪,让她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
但我错了。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用她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对命运的反击。她没有哭闹,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最踏实、最辛苦的一条路,去实现那个“回家”的愿望。
她说的独立,不是大卫口中那种冷冰冰的、美式的“独立”,而是一种带着中国孩子特有的韧性和对家的眷恋的、了不起的独立。
我为她的成长感到骄傲,又为她的辛苦感到心疼。两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我泣不成声。
挂了电话,我把安娜打工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
我妈听完,捂着嘴就哭了。我爸则沉默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最后,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对我说:“给孩子把钱打过去。告诉她,机票的钱,家里出。让她好好读书,别那么辛苦了。”
我点了点头。
那个晚上,我想了很久。
我意识到,我必须去见她。我不能再隔着屏幕,去想象她的生活。我要亲眼看看她,抱抱她。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遏制。
国境线可以阻拦她回来,但它,拦不住我奔向她的脚步。
第6章 没有终点的旅程
做出决定后,我立刻开始行动。
请假、办签证、订机票……所有的事情,我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去推进。单位的领导很理解我的情况,爽快地批了我的长假。签证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半个月后,我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心无比平静。这趟旅程,和我们上次失败的归途,心情截然不同。那一次,是充满期待的回家;这一次,是义无反顾的奔赴。
经过十四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走出到达大厅,我一眼就看到了在人群中等待的安娜。
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围着围巾,冻得鼻尖通红。看到我,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睁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奇迹。
她飞奔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妈妈!”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巨大的惊喜。
我抱着她,感受着她真实的体温和心跳,感觉这几个月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所有的思念、担忧和心疼,都在这个拥抱里,得到了安抚。
“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埋在我怀里,不停地问。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摸着她的头发,笑着说。
我们坐上了去她学校的大巴。路上,她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兴奋地跟我讲着她这几个月的生活。讲餐馆里的趣事,讲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客人,讲她如何用蹩脚的中文和后厨的师傅们交流。
她的讲述里,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只有一种经历过后的豁达和乐观。
我静静地听着,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陌生街景,心里无比确定: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我没有让她带我去她打工的餐馆,也没有让她退掉宿舍。我只是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住了下来。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给她做饭。
我逛遍了附近的亚洲超市,买来各种各样的调料和食材。我给她做她心心念念的红烧肉、咸笃鲜,包她最爱吃的荠菜馄饨。
小小的公寓里,第一次飘起了真真切切的、属于中国的饭菜香。
安娜每天一下课就跑回来,像一只归巢的小鸟。我们俩挤在小小的厨房里,一起择菜,一起包馄饨。她会跟我分享学校里的一切,我也会跟她讲家里外公外婆的近况。
我们就像在上海的家里一样,过着最平凡也最温馨的日子。
我没有问她关于国籍的想法,也没有再提回国的事情。我们都默契地回避着那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只是珍惜着当下这来之不易的团聚时光。
我住了一个月。签证到期前,我必须离开。
离别的那天,还是在机场。
和上次不同,这一次,我们俩都表现得很平静。
“妈妈,你放心回去吧。”安娜帮我整理着衣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等我放暑假,我就去看你。”
“去看我?”我愣了一下。
“对啊,”她笑了,眼睛亮晶晶的,“我可以用自己打工挣的钱,买机票,去中国‘旅游’啊。虽然我不能‘回家’,但是我可以去‘看我妈妈’,对不对?”
她俏皮地眨了眨眼。
我看着她,忽然就笑了。
是啊,条条框框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一种身份的门被关上了,但我们总能找到另一扇窗。
回家,或者旅游,或者探亲。称呼是什么,又有什么重要呢?重要的是,我们想见彼此的心,和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妈妈等你。”
我们拥抱告别,没有流泪。
我转身,走进安检口,没有回头。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飞机再次升空,我看着舷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一片澄明。
这几个月,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考验着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都曾迷茫、痛苦、绝望。但最终,我们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安娜学会了独立和担当,我学会了放手和信任。我们都更深刻地理解了“家”的含义。
家,不是一本护照,不是一个地理位置。
家,是那个愿意为你洗手作羹汤的人,是那份无论相隔多远都斩不断的牵挂,是那种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奔赴万里的决心。
我的女儿是外国籍,我不知道下一次她什么时候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
但那又怎样呢?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无论她在哪里,我都知道,她总会找到回家的路。而我,也永远会是她归途上,那盏不灭的灯。
本文标题:5岁女童去上海探亲 3天走丢3次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26156.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