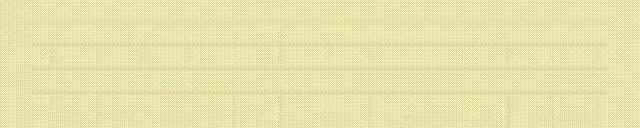一百万台币
那枚硬币躺在我的手心,带着一种陌生的、轻飘飘的金属质感。
二十块。
新台币。
我二舅公,陈建勋,一个只在父亲口中存在了几十年的符号,此刻就站在我面前。他刚从那架延误了两个小时的飞机上下来,一身熨帖的浅色休闲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尽管眼角和脖颈的皮肤已经松弛,但那股劲儿端着,像个老派的绅士。
他把那枚硬币“甩”给我,可能这个词有点过分,但那个动作确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随意。
“阿默,是叫阿默吧?”他操着一口软糯又带着奇特咬字的台湾腔普通话,审视着我,像在看一件待估价的古董,“拿着,去买几个茶叶蛋吃,你们这里机场的东西,贵得离谱吧?这个,够你吃三个了。”
我爸,林国栋,在我身边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脸上的笑几乎要堆不住。
“哎呀,二叔,您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
二舅公摆摆手,打断我爸的客套,眼神依旧停留在我脸上,带着一丝探究和……怜悯?
对,是怜悯。
我捏着那枚硬币,指尖冰凉。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中央空调,冷气开得像不要钱。头顶巨大的穹顶下,人来人往,拉杆箱的轮子滑过光洁的地砖,发出持续不断的嗡鸣。一切都现代得不像话,一切都昂贵得明码标价。
而我,一个在陆家嘴金融中心上班、月薪足够买下几千个茶叶蛋的所谓“白领”,被我素未谋面的台湾亲戚,当众打赏了二十块新台币。
用来买三个茶叶蛋。
我突然很想笑。
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愤怒的笑,是一种荒谬到了极点,连生气都觉得多余的笑。
我妈在旁边轻轻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阿默,快谢谢二舅公啊。”
我抬起头,看着二舅公那张写满“优越感”的脸,努力挤出一个我认为还算得体的微笑。
“谢谢二舅公。”
我说。
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然后我把那枚硬币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钱包夹层里,好像那是什么珍贵的纪念品。
二舅公似乎对我的“乖巧”很满意,点了点头,终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开始指挥他身后的儿子和老婆。
“文轩,行李看好,不要被人顺走了。”
“阿玲,你的包,背在前面。”
他儿子,我的表哥陈文轩,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有些尴尬地对我笑了笑。他爸的声音不大,但那种警惕和防备,像针一样扎人。
这里是上海,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我爸已经热情地迎上去,要接过二舅公手里的一个小行李箱。
“二叔,我来我来!一路辛苦了!家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
二舅公象征性地推让了一下,还是把箱子递给了我爸。
“国栋啊,几十年不见,你也老了。”他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语气里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感慨。
我爸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是啊,二叔,您走的时候,我才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下,“我爸到走都念叨您呢。”
我爷爷,那个沉默寡言的老木匠,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总坐在院子里的那张旧藤椅上,对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发呆。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土布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爷爷,另一个,就是他唯一的弟弟,陈建勋。
不,那时候他还叫林建勋。
后来,风云变幻,兄弟俩一个留在了大陆,一个跟着溃败的队伍去了海的另一边。从此,一个姓林,一个随了母姓,姓陈。
几十年来,只通过几次辗转香港的信件,知道彼此还活着。
现在,这个活在传说里的亲戚,终于回来了。
带着他的优越感,和二十块新台pe币。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都是消毒水和香水混合的味道。
我对自己说,林默,冷静。
他是长辈,是爷爷念叨了一辈子的人。
为了你爸。
忍。
车是我开来的,一辆德系的SUV,不大,但在上海这种地方,也算个体面的代步工具。
我爸本来想叫专车的,我觉得没必要,自己家有车,方便。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
当我打开后备箱,准备放行李的时候,二舅公又发话了。
“哟,国栋,现在混得不错嘛,都开上四个圈了。”他绕着我的车走了一圈,伸手在车门上摸了摸,像在检查漆水的成色,“这车,在你们这里,要不少钱吧?贷款买的?”
我爸的脸僵了一下,连忙解释:“不是我的,是阿默的。她自己买的。”
“哦?”二舅公的眉毛扬得更高了,重新把目光投向我,那眼神,比刚才更复杂了,“女孩子家家,开这么好的车?你们这里的老板,对员工很大方哦。”
这话说的,简直就是淬了毒的棉花。
我妈的脸色也变了。
我站在后备箱前,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
什么叫“老板对员工很大方”?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二舅公,我没老板。我自己就是老板。”
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说老板是抬举自己,但至少,这车,这房,是我一笔一笔画图,一个一个项目熬夜换来的。跟任何“老板”都没关系。
空气瞬间凝固了。
二舅公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直接顶回来。
我爸赶紧打圆场:“哎呀,小孩子家乱说的,什么老板,就是自己搞个小工作室,瞎折腾。”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把我往旁边推,自己抢着把行李塞进后备箱,“二叔,二婶,文轩,快上车吧,外面热。”
二舅婆,一个看起来很精明干练的女人,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只是用一种评估的眼神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此刻她拉了拉二舅公的袖子,低声说了句什么。
二舅公“哼”了一声,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一路上,车里的气氛都很诡异。
我爸和我妈努力找着话题,从上海的天气,说到台湾的风光,二舅公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
台湾什么都好。
“你们这里空气不行啊,灰蒙蒙的,在台北,我们阳明山上的空气,甜的。”
“高楼盖得是不少,但看起来都一样,没什么特色。我们的101,那才是地标。”
“路这么堵,管理水平要加强啊。我们那里,机车都比你们汽车跑得快。”
我爸在一旁赔着笑,不断点头。
“是是是,上海人太多了,肯定没法跟台北比。”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我真想一脚油门踩到底,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大陆的“推背感”。
我瞥了一眼后视镜,表哥陈文轩低着头在玩手机,似乎对这场对话毫无兴趣,甚至有点想把自己藏起来。
终于,车开进了我们家的小区。
一个还算体面的中产小区,绿化做得不错,楼间距也宽。
二舅公透过车窗,又开始了他的点评。
“这个小区,看起来还行。物业费不便宜吧?”
我妈赶紧回答:“还行还行,一个月几百块。”
“几百块人民币?”二舅公咂了咂嘴,“那跟我们那边也差不多了。不过你们的收入……”
他没说下去,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你们挣那么点钱,还住这么贵的地方,打肿脸充胖C子。
我把车停进地下车库,熄了火。
车里一片寂静。
我爸解开安全带,回头,脸上还是那种近乎讨好的笑。
“二叔,到了,我们先回家放行李,晚上我订了馆子,给您和二婶接风洗尘。”
晚上的接风宴,我爸下血本订在了黄浦江边的一家本帮菜馆,包厢的窗户正对着陆家嘴的璀璨灯火。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三件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江面上的游船拉着长长的光影,流光溢彩。
我以为,这样的景色,总能让他闭嘴了吧。
我错了。
菜一上来,二舅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国栋啊,太浪费了,点这么多菜做什么?我们一家人,随便吃点就好。”
他嘴上说着浪费,筷子却没停。夹起一块熏鱼,放进嘴里,细细品了品。
“味道还行,就是太甜了。我们台湾的菜,讲究的是原味,清淡。”
他又夹起一只水晶虾仁。
“这个,用的是河虾吧?我们那边都吃海虾的,肉质比较Q弹。”
我爸的笑容已经有点挂不住了,只能不停地给他布菜。
“二叔,您尝尝这个,蟹粉豆腐,我们上海的特色。”
“哦,螃蟹啊。”二舅公放下筷子,喝了口茶,“我们那里的万里蟹,现在正是季节,那个鲜美……唉,不说了,说了你们也没吃过。”
我坐在那里,一口菜都吃不下去。
胃里像堵了一团火。
我只想把桌子掀了。
我妈不停地在桌子底下踢我,示意我忍耐。
表哥陈文轩倒是吃得挺开心,一边吃还一边小声跟我说:“表姐,这个红烧肉好吃,比我们楼下张伯伯做的好吃。”
我看了他一眼,他眼神很真诚,不像他爸。
或许,下一代,总会有点不一样。
就在这时,二舅公把话题转向了我。
“阿默啊,刚刚听你爸说,你自己搞工作室?”
我点点头,没说话。
“做什么的?设计?”他问。
“室内设计。”
“哦,装潢嘛。”他用了一个很古早的词,“那很辛苦的,要跑工地,跟工人打交道,女孩子做这个,不容易。”
“还好。”我淡淡地说。
“一个月,能挣多少啊?”他终于问出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爸赶紧插话:“哎呀,二叔,问这个干嘛,小孩子家挣点零花钱罢了。”
“我问问嘛,关心一下小辈。”二舅公不依不饶地看着我,“在上海这种地方,消费那么高,一个月没个一两万人民币,怕是活不下去吧?”
他的语气,仿佛一两万人民币是个天文数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悲。
他不是坏,他只是……被困在了时间的琥珀里。
他的认知,他的优越感,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台湾人是“台巴子”(此处指有钱的台湾同胞)的年代。
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时代早就变了。
他眼里的“大陆”,还是那个贫穷、落后、需要他来“施舍”二十块钱买茶叶蛋的地方。
而我们,早就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了。
我拿起公筷,给二舅公夹了一块他最看不上的“太甜”的红烧肉,放在他面前的骨碟里。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二舅公,我一个月挣的钱,可能不多。”
“也就够在这陆家嘴,买个厕所吧。”
我说的是实话,甚至还谦虚了。
整个包厢,瞬间鸦雀无声。
只剩下窗外黄浦江上,游船的汽笛声,悠长地传来。
二舅公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顿饭最终是不欢而散的。
我爸的脸色比二舅公还难看。
回家的路上,车里死一般的寂静。
一进家门,我爸就把客厅的灯全部打开,亮如白昼。
他没换鞋,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玄关,指着我。
“林默!你今天晚上!是什么态度!”
他的声音在发抖,是气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二叔!是你爷爷唯一的弟弟!我们盼了多少年才盼来他!你就是这么给他接风的?”
我妈赶紧上来拉他,“国栋,你小点声,邻居都听见了。阿默也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闭嘴!”我爸一把甩开我妈的手,“就是你惯的!看看她现在像什么样子!有点钱了不起啊?目无尊长!口无遮拦!”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爸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一片冰凉。
“我怎么了?”我问,声音很平静,“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说错什么了?”我爸气得笑了起来,“你在饭桌上那么说,是想干什么?打你二舅公的脸吗?让他下不来台,你就开心了?”
“是他先让我下不来台的。”我说,“从机场开始,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哪一样是尊重我们了?茶叶蛋?贷款买车?老板大方?爸,你都听见了,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反应?跪下来谢谢他的‘关心’吗?”
“他是长辈!他几十年没回来了,他对大陆不了解,说错几句话怎么了?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你让着他点会死吗!”
“我让了。”我说,“在机场,他说茶叶蛋的时候,我让了。在车库,他说我被老板包养的时候,我也让了。在饭桌上,他把我们上海说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我还在让。爸,我也是人,我有自尊。我的自尊,就那么不值钱吗?在你眼里,维护一个几十年不见的所谓‘亲戚’的面子,比你女儿的尊严更重要吗?”
“你……”我爸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那是我亲二叔!”他最后吼了出来,带着一丝绝望,“你爷爷临死前,还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找到他!我找到了!我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家,我们大陆这边,都是一群没教养的白眼狼!”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忽然明白了。
我爸不是在维护二舅公。
他是在维护他自己心里那个关于“亲情”的、脆弱的梦。
他害怕这个梦碎了。
而我,亲手把它敲出了裂缝。
“爸,”我的声音软了下来,“我累了,我先回房了。”
我转身,不想再跟他争辩。
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成了一个低气压中心。
二舅公一家住在我家对面的酒店里,我爸本来想让他们住家里的,但二舅公嫌我们家“地方小,不方便”,坚持住了酒店。
我爸每天早早地就去酒店“请安”,然后陪着他们到处逛。
豫园、城隍庙、新天地、武康路……上海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景点,我爸都跟个导游一样,鞍前马后地陪着。
而我,成了这个家里的隐形人。
我爸不跟我说话,我妈唉声叹气,想劝又不知道从何劝起。
我乐得清静,每天正常去工作室上班,加班,回家。
只是,那个家,感觉越来越像一个冰冷的旅馆。
周五晚上,我加完班回到家,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
不光是我爸妈和二舅公一家,还有我大伯、我姑姑他们,满满当当一屋子。
气氛很热烈。
二舅公坐在沙发的正中央,正在“开坛讲法”。
“……所以说啊,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那是全世界都羡慕的。你们这里看病,很贵吧?我听说,没个几十万,大病都不敢生?”
大伯和我姑姑连连点头,脸上带着羡慕和向往。
“是啊是啊,现在看病是贵。”
“我们这医保,报不了多少。”
我换了鞋,想直接溜回自己房间。
“阿默回来了?”我爸看见了我,语气生硬地叫住我,“过来,坐。”
我没动。
“过来!”他加重了语气。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走过去,在离他们最远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
二舅公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带着一丝得胜的意味。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不光是医疗,还有教育。我们台湾的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就接受的是‘爱的教育’,不打不骂,鼓励创造力。所以你们看文轩,虽然内向一点,但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拍了拍坐在旁边的陈文轩。
陈文轩的脸红了,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姑姑立刻接话:“可不是嘛!我们这边的小孩,作业多得做不完,天天补课,压力大死了!你看我孙子,才上小学,就戴上眼镜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什么“爱的教育”?台湾的升学压力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补习班文化更是盛行了几十年。他说的,是他想象中的台湾,还是他想让我们相信的台湾?
我拿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
眼不见为净。
“阿默!”我爸又叫我,“长辈说话,你玩什么手机?懂不懂规矩?”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
“爸,我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很累。你们聊,我听着就行。”
“你……”
“哎,国栋,算了算了。”二舅公假惺惺地出来当和事佬,“年轻人嘛,工作辛苦。阿默啊,你那个设计室,生意好不好啊?”
又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还行。”
“还行是多好啊?”他追问,“要不要二舅公帮你介绍点门路?我在台北认识很多老板,他们在那边都有厂房、办公室,需要‘装潢’的。你去我那边,肯定比在上海有前途。”
他看着我,脸上带着“我是在提携你”的恩赐表情。
“我们那边,设计师很受尊重的,收入也高。像你这样的,努力一点,一年挣个一百万……新台币,不成问题。”
一百万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万。
我工作室一个稍微大点的项目,都不止这个数。
客厅里所有亲戚的眼睛都亮了。
“哎哟,那敢情好啊!”大伯说,“阿默,快谢谢你二舅公!”
“是啊是啊,多好的机会!”姑姑也附和。
我爸的脸上也露出了期待的神色。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我们父女和解的契机。只要我顺着台阶下,接受二舅公的“好意”,这个家就能恢复和平。
我看着满屋子亲戚殷切的脸,看着我爸近乎哀求的眼神。
我再看看二舅公。
他靠在沙发上,嘴角微微上扬,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掌控一切的感觉。
他不是在提携我。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再次证明他的优越,再次把我,把我们这些大陆亲戚,踩在脚下。
他要我低头。
要我承认,我在这里的奋斗,我的一切,都不如他随口许诺的一个“机会”。
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根弦,断了。
我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走到茶几前,从钱包里,拿出了那枚我珍藏了几天的,二十元新台币硬币。
我把它放在了茶几的玻璃台面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声音不大,但在瞬间安静下来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二舅公,”我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得像冰,“谢谢您的‘好意’。”
“这个,还给您。”
我指着那枚硬币。
“您说,它够我买三个茶叶蛋。”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在上海,一个最普通的便利店茶叶蛋,也要三块钱人民币。三个,就是九块。按照今天的汇率,二十块新台币,大概是四块六毛钱人民币。”
“所以,这笔钱,连两个茶叶蛋都买不起。”
我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客厅里目瞪口呆的亲戚们。
“我之所以跟您说这个,不是为了计较几块钱。”
“我是想告诉您,您眼里的‘大陆’,可能还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吃不起茶叶蛋,台湾在大家眼里,是遍地黄金的天堂。”
“但是,二舅公,时代变了。”
“您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我长大的这个城市,早就不是您想象中的样子了。我们用移动支付,出门可以不带钱包;我们坐高铁,几个小时就能跨越上千公里;我们有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有自己的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我,林默,”我指着自己,“我在这座城市有房有车,有自己的事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我不辛苦,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也不需要去任何人手下讨生活,尤其是一个连茶叶蛋价格都搞不清楚的人。”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我爸那张煞白的脸上。
“爸,对不起。”
“我不能为了维护您心中那个虚幻的‘亲情’,就扭曲我自己,否定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真正的亲情,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上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和怜悯。”
“如果所谓的‘亲情’,需要我跪着去维持,那我宁可不要。”
说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对二舅公,而是对我所有的长辈。
“抱歉,失陪了。”
然后,我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靠在门板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说出那番话。
我只知道,如果不说,我会憋屈死。
门外,一片死寂。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我爸压抑的怒吼,我妈的哭劝,还有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关门声。
他们走了。
那天晚上,我爸没有来敲我的门。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
餐桌上,留着我妈给我做的早饭,已经凉了。
我默默地吃完,然后去上班。
工作室里,合伙人阿K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说没事。
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画图,改方案,跟客户开会。我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但只要一停下来,我爸那张失望到极点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太不孝了?
晚上,我收到了表哥陈文轩的微信。
他的头像是只可爱的柴犬。
“表姐,对不起。”
这是他发来的第一句话。
我愣了一下,回过去:“你道什么歉?”
“为我爸的言行,向你道歉。他那个人……唉,就是老脑筋,被困在过去了,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我回了两个字。
“表姐,你今天说得很好。真的。”他很快又发来一条,“其实,我很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敢说真话,羡慕你活得那么……有底气。不像我,毕业了找不到喜欢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公司帮忙,每天被我爸念叨。他说大陆这不好那不好,其实他自己也好几年没拿到什么像样的项目了,全靠以前的老本撑着。这次来,也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久久没有回复。
原来,那身熨帖的衣服,那端着的架子,那口口声声的优越感背后,是这样的底色。
不是强大,而是虚弱。
不是自信,而是心虚。
他不是来“视察”的,他是来“取经”的,却又放不下那可怜的自尊,只能用攻击和贬低,来维持自己最后的体面。
何其可悲。
“表姐,我们明天就回去了。机票改签了。”
“哦。”
“我爸说,他再也不来大陆了。”
“……”
“但是,表姐,我以后会常来的。我觉得上海很棒,比台北好玩多了。”
最后,他发来一个笑脸的表情。
我对着那个笑脸,也笑了。
或许,这趟天翻地覆的探亲之旅,也不是全无收获。
至少,让我认识了一个还算可爱的表弟。
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
我爸也没叫我。
我们之间的冷战,还在继续。
一个星期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声音疲惫。
“阿默,你爸病了。”
我心里一咯噔,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怎么了?什么病?严重吗?”
“老毛病,高血压犯了,头晕。在医院挂水呢。”
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我爸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几天不见,他好像老了十岁。
我妈坐在一旁,眼圈红红的。
看到我,我爸睁开了眼睛,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我走过去,给他倒了杯水。
“爸,喝点水吧。”
他没理我。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对我妈说:“妈,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这里我守着。”
我妈看了看我爸,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父女俩。
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胸口。
过了很久,我爸开口了,声音沙哑。
“你二舅公,小时候,对我最好。”
我没说话,静静地听着。
“那时候家里穷,有什么好吃的,他都偷偷留给我。有人欺负我,他第一个冲上去跟人打架。他走的那天,在码头上,塞给我一把弹珠,那是他赢了一整个夏天的宝贝。他说,等他回来,要给我带巧克力。”
“我等了半辈子,没等到他的巧克力,只等到他客死异乡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是误传。我找到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觉得我对我爸,对死去的爷爷,有个交代了。”
他的眼角,有泪滑落。
“我只是……我只是想让他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走。我只是想让他看看,我们过得不比他差。我只是想……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可是,全被你搞砸了。”
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爸,对不起。”
我哽咽着说。
“我只想着我自己的委屈,我没想过你。”
“我以为,你让我忍,是因为你懦弱,是因为你看重那个所谓的‘亲戚’超过我。我不知道,你心里背着这么重的包袱。”
我终于明白,那场争吵,我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在说“尊重”,他在说“情义”。
我在说“现在”,他在说“过去”。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我们站在了时间的河流的两岸,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彼此对望,谁也无法真正地理解谁。
“爸,是我不好。”我握住他冰凉的手,“我不该那么冲动,不该让您那么难堪。”
我爸没有抽回手。
他看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
“其实,那天晚上,你走了以后。你表哥文轩,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你二舅公的公司,这几年一直亏损。他说,你二舅公在台湾,也经常跟人吹牛,说他在大陆有个多厉害的侄子,多能干的侄女。”
“他说,你二舅公这次来,带了所有的积蓄,想在上海投资个小生意,东山再起。所以他才那么……急于证明自己。”
我愣住了。
那个高高在上,用二十块台币打发我的二舅公,竟然是这样一个外强中干的形象。
“他走的时候,托文轩转交给我一个信封。”
我爸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旧旧的信封。
他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人民币,不厚。
还有一张信纸。
信纸上,是二舅公那手龙飞凤舞的字。
“国栋吾弟:
匆匆一别,未能尽言。此次前来,本想光耀门楣,未曾想,徒增笑料。时代变迁,吾辈已老,观念陈腐,望弟及侄女见谅。
阿默是个好孩子,有骨气,像当年的大哥。吾心甚慰。
信封内薄资,乃二叔一点心意,为你父亲当年医药费,迟到了四十年,聊胜于无。
望多保重。
兄,建勋。”
信的最后,还附了一行小字。
“另,那二十元台币,本是想让阿默留作纪念。台湾年轻人现在流行收集特殊年份的硬币。茶叶蛋之说,实乃吾之不当玩笑,切勿当真。”
我捏着那张信纸,手在抖。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信纸上,晕开了一团团墨迹。
原来,那句最伤人的话,只是一个笨拙的、自以为是的玩笑。
原来,那份最刺眼的优越感,只是一层保护色。
原来,在那层坚硬的、讨人厌的外壳下,也藏着一颗想要靠近,却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的心。
我哭得泣不成声。
我爸拍了拍我的手。
“傻孩子。”他说,“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
出院那天,我去接我爸。
阳光很好,透过车窗洒进来,暖洋洋的。
我爸坐在副驾驶,精神好了很多。
“阿默,”他突然说,“那二十块钱,还在吗?”
我点点头,从钱包夹层里,拿出了那枚硬币。
在阳光下,它闪着温润的光。
“收好了。”我爸说,“等你二舅公下次来,你再还给他。”
“他还来吗?”
“来。”我爸笑了,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他说了,下次来,不谈别的,就想尝尝你说的,那个能买下陆家嘴一个厕所的设计,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看着前方宽阔的马路,车流不息。
远方,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轮廓分明,直插云霄。
我笑了。
“好。”
我说。
本文标题:一百万台币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29229.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