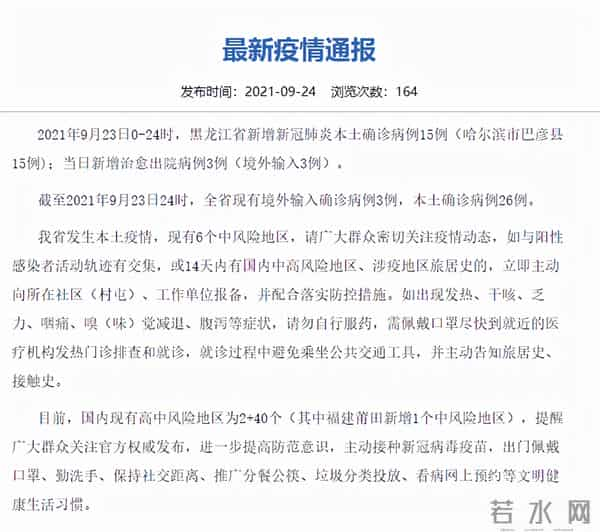女子用头砸西瓜把自己送进医院
那年夏天,热得像个发了疯的蒸笼。
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烦意乱,好像在嘲笑我,嘲笑我那张比录取分数线低了十二分的高考成绩单。
我爸的腿是在工地上摔断的,钢筋穿过了小腿,白森森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
家里那点微薄的积蓄,像水一样泼进了医院这个无底洞。
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根还没长结实、被现实压得嘎吱作响的烂木头。
我唯一的活儿,就是守着家里的三亩西瓜地。
白天顶着毒太阳锄草、浇水,晚上就睡在瓜地边上那个用油毛毡和破木板搭起来的窝棚里,防贼。
贼偷瓜是小事,主要是防村里那几个手欠的半大小子,他们不偷,他们就喜欢搞破坏,一脚能给你踩烂好几个。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浑身都是汗臭和泥土味,未来像被蚊子叮咬后挠破的伤口,又痛又痒,还流着脓。
窝棚里点了盘最劣质的蚊香,烟气呛人,但总比被蚊子抬走强。
我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大裤衩,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竹床上,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
月光从窝棚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投下几道惨白的光斑。
远处的蛙鸣和近处的虫叫,交织成一首催眠曲,但我睡不着。
心里堵得慌。
就在我快要被这股烦闷逼疯的时候,窝棚外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很轻,像小猫走路。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抓起床边的砍柴刀。
这年头,人心比鬼都恶。
“谁?”我压低了嗓子,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外面没动静了。
只有风吹过瓜秧的沙沙声。
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心想可能是只野猫或者黄鼠狼。
刚准备躺下,那个声音又响了,这次更近,就在窝棚门口。
我攥紧了刀柄,手心里全是汗。
门帘,一块破麻布,被一只手轻轻掀开了。
一个身影,逆着月光,慢慢地钻了进来。
我看不清她的脸,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洗发水香味,不是村里女人用的那种廉价皂角的味道。
是个女的。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脑子里一团乱麻。
这深更半夜的,一个女的跑我这瓜棚里来干什么?
“陈默?”
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发颤,但很好听。
我愣住了。
这个声音我熟。
是林晚秋。
我们村的林晚秋。
村长的女儿,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是我们村所有长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眼睛像含着水,不像我们这些在土里刨食的,一个个都晒得跟黑炭似的。
从小到大,她都是白天鹅,我就是那只躲在泥塘里的癞蛤蟆。
我们俩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现在,这只白天鹅,半夜三更地钻进了我的癞蛤蟆窝。
“林晚秋?”我几乎不敢相信,“你……你来干啥?”
她没说话,慢慢走到我床边。
窝棚里很暗,我只能看到她一个模糊的轮廓,还有那双在黑暗里也亮得惊人的眼睛。
她好像在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更懵了,手里的刀也不知道是该放下还是该继续举着。
“你……你咋了?谁欺负你了?”
虽然跟她不熟,但一个女孩子半夜哭着来找你,是个爷们儿都不能干看着。
她还是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我。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氛围,混杂着汗味、蚊香味、泥土味,还有她身上那股好闻的洗发水味。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感觉自己光着的膀子在发烫。
“你要不……先坐下?”我往床里面挪了挪,拍了拍空出来的地方。
竹床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呻吟。
她依言坐下了,离我隔着一拳的距离。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还有轻微的颤抖。
“到底咋了?”我又问了一遍。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
“陈默。”
“嗯?”
“你……你敢不敢?”
“敢不敢啥?”我一头雾水。
她猛地抬起头,月光恰好从一个破洞里照在她脸上。
我看见她满脸的泪痕,眼睛又红又肿,嘴唇被她自己咬得发白。
那是一种绝望又疯狂的眼神。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她说:“陈默,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了。
像被人迎面抡了一记大铁锤。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这鬼天气把我热糊涂了,出现了幻觉。
“你……你说啥?”
“我说,”她一字一顿,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窝棚里,却像惊雷一样,“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傻了。
彻底傻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手里的蒲扇掉在了地上都不知道。
这是林晚秋?那个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林晚秋?
那个我只敢在背后偷偷多看两眼的林晚秋?
她要跟我……生米煮成熟饭?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你喝多了吧?”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没喝酒。”她摇摇头,眼神异常清醒,“我很清醒,陈默,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那你就是疯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这事儿太离谱了,离谱到让我觉得害怕。
“对,我就是疯了。”她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再不疯,我就要死了。”
我看着她,心里那点旖旎的念头瞬间被一股寒意取代。
她不是在开玩笑。
她是真的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
“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个被吓坏的傻子。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
然后,她幽幽地说:“我爸,要把我嫁给镇上那个王老板的儿子。”
王老板我听说过,开水泥厂的,有钱,在镇上横着走。
他那个儿子叫王建军,我也见过,染着一头黄毛,走路晃着膀子,看人的眼神跟看牲口一样,听说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还打过人。
“他……他凭什么?”
“凭他爸能给我爸弄到县里那个建材站站长的位置。”林晚秋的声音里充满了嘲讽和悲凉。
我明白了。
彻头彻尾的交易。
用女儿的幸福,去换自己的前程。
这种事,在我们这儿,不算新鲜。
“那你也不能……”我后面的话没说出口。
不能来找我啊!
我们村那么多年轻人,有比我长得帅的,有比我家境好的,为什么偏偏是我?
一个高考落榜,前途一片黑暗的穷小子。
“因为他们都怕我爸。”林晚秋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村里这些小伙子,哪个见了我不像老鼠见了猫?也就你……”
她顿了顿,看着我,“也就你,见了我就跟见了空气一样,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我心里苦笑。
我不是懒得抬,是不敢抬。
自卑,你知道吗?
“而且,”她继续说,“你虽然考砸了,但你以前学习很好,你脑子聪明。你不是个坏人。”
“所以你就想拉我下水?”我忍不住刺了她一句。
“是。”她承认得坦荡,“陈默,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我的竹床上。
“如果我嫁给王建军,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宁可死,也不嫁给他。”
“我不想死,我还想上大学,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只要……只要我们把事儿办了,我爸就拿我没办法了。到时候他为了脸面,也只能认了。”
“你放心,我不要你负责,等我上了大学,毕了业,我挣了钱就还你,我给你补偿。”
她像是在交代遗言,语无伦次,颠三倒四。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有同情,有愤怒,也有一丝被“选中”的荒谬感。
我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脸,那张曾经让我觉得遥不可及的脸,现在就在我面前,脆弱得像一张薄纸。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心动了。
不是那种龌龊的念头,而是一种冲动。
一种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一种想跟这个操蛋的现实干一架的冲动。
凭什么有钱有势就能为所欲为?
凭什么一个好好的姑娘就要被当成货物一样交易?
“你……你想清楚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想清楚了。”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眼神却无比坚定。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我深吸了一口气,窝棚里那股呛人的蚊香味,似乎也没那么难闻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能听到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还有她急促的呼吸声。
月光下,她的脸庞白得发光,嘴唇微微张着,像是在等待一个宣判。
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陈默,你疯了吗?这是村长的女儿!你掺和进去,林老拴能扒了你的皮!你爸妈怎么办?你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另一个小人儿说:陈默,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一个姑娘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眼睁睁看着她往火坑里跳?你这辈子良心能安吗?反正你现在也是一无所有,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两个小人儿吵得我头疼。
我使劲摇了摇头,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都甩出去。
“林晚秋,”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一旦做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知道。”
“你爸会打死我的。”
“他不敢。”她咬着牙,“事情闹大了,他比谁都丢脸。”
“那王建"un呢?”
提到这个名字,她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
“他就是个混蛋,是个。”
我沉默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王建军那样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他知道林晚秋为了躲他,和我……
我不敢想下去。
“陈默,”她忽然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很凉,还在发抖,“求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用这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话。
那个骄傲的、优秀的、像白天鹅一样的林晚秋,在向我这只癞蛤蟆求救。
我心里的那道防线,彻底崩塌了。
“你起来。”我说。
她愣住了。
“你先起来。”我又说了一遍。
她慢慢地站起身,不解地看着我。
我也站了起来,在狭小的窝棚里,我们几乎要撞在一起。
我没看她,径直走到窝棚门口,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外面的空气比里面凉快多了,带着西瓜的清甜和泥土的芬芳。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脑子冷静下来。
她也跟着走了出来,站在我身后,不敢说话。
我指着满地的西瓜,对她说:“你看到这些瓜了吗?”
她点点头。
“我爸的腿断了,家里所有的指望,都在这些瓜身上了。”
“一个瓜卖好了,能换回一袋化肥,一张膏药。”
“我要是出了事,这些瓜没人管,我爸的腿没人管,我妈会哭死。”
我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林晚秋的头垂得更低了,肩膀又开始抽动。
“对不起……”她小声说,“我……我没想那么多……”
“你当然没想那么多。”我转过身,看着她,“你只想着你自己。你想着怎么逃出火坑,你想着你的大学,你的未来。”
“我不是……”她想辩解,但声音弱得像蚊子叫。
“你就是。”我打断她,“你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反正已经烂到底了,再烂一点也无所谓,是吗?”
“不是的!陈默,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她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只是……我只是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好人就活该被你拖下水吗?”我甩开她的手,声音不由得大了起来。
她被我吼得后退了一步,愣愣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又有点不忍。
我他妈的,就是心软。
我叹了口气,蹲下身,从瓜藤下摸出一个熟透了的西瓜。
“啪”的一声,我用拳头把它砸开。
红色的瓜瓤,黑色的瓜子,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诱人。
我掰了一半递给她。
“吃吧。”
她没接,就那么看着我。
“吃啊。”我又说了一遍,“大半夜跑来,不渴吗?”
她这才犹豫着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
汁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她也顾不上擦。
我也拿起另一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的甜。
甜得发苦。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就在这片静悄悄的瓜地里,啃着一个用拳头砸开的西瓜。
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
“陈默。”她先开了口。
“嗯。”
“对不起。”
“行了,别说了。”我把啃完的瓜皮扔到一边,“再说就没意思了。”
她也把瓜皮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
“那……那我回去了。”她小声说。
“回去?”我冷笑一声,“你现在回去,明天等着你爸把你绑上车,送到王建军床上?”
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那我怎么办?”她带着哭腔问。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我和她,其实是一样的人。
都是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的倒霉蛋。
只不过她想反抗,而我,已经快要认命了。
“办法,不是没有。”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光。
“什么办法?”
“你不是说,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你爸就没辙了吗?”
她愣愣地点点头。
“那我们就把这饭,煮得再真一点。”
“什么……什么意思?”
“明天一早,”我看着远处的村庄轮廓,一字一句地说,“你就跟你爸说,你怀孕了。”
林晚秋的嘴巴张成了“O”型,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怀……怀孕了?”她结结巴巴地问,“怀……怀谁的?”
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的。”
她彻底石化了。
过了好半天,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陈默,你……你是不是也疯了?”
“我没疯。”我说,“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你爸顶多是为了脸面,捏着鼻子认了。但他心里肯定恨死我,以后有的是办法收拾我。”
“但如果你只是‘怀孕’了,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
“他肯定会逼问你,会打你,会骂你。你就咬死了,说孩子是我的。那天晚上你来找我,村里肯定有人看见了,这就是证据。”
“他会来找我,找我爸妈。到时候,我们就演一场戏。”
“演戏?”
“对,演一场悔不当初、愿意负责、但是穷得叮当响的苦情戏。”我冷笑着说,“我要让他觉得,把你嫁给我,比嫁给王建军还让他丢脸,还让他亏本。”
林晚秋呆呆地听着我的“计划”,眼神从震惊,到疑惑,再到一丝佩服。
“他……他会信吗?”
“他会的。”我笃定地说,“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俩是在演戏。在他眼里,我就是个被荷尔蒙冲昏了头的穷小子,而你,就是个不知廉耻的傻姑娘。”
“这个计划……太冒险了。”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反问她。
她沉默了。
是啊,她没有别的办法了。
“陈默,”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是帮你。”我别过头,不去看她的眼睛,“我是在帮我自己。”
“帮你自己?”
“对。”我看着天边那抹即将泛起的鱼肚白,“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待在这瓜地里,被所有人当成一个废物。”
“林晚秋,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敢。”
那一晚,我们没有把生米煮成熟饭。
但我们点燃了一把火。
一把可能会把我们自己都烧成灰烬的火。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晚秋就回去了。
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陈默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平静了。
我在瓜棚里坐立不安地等了一上午。
太阳越升越高,瓜棚里像个烤炉,但我心里却一阵阵发冷。
果然,中午刚过,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
是我妈的声音,她在喊我回家吃饭。
但那声音,抖得厉害,还带着哭腔。
我知道,事儿来了。
我抄起砍柴刀,不是为了壮胆,就是个习惯。
然后,我一步一步,朝家里走去。
还没到家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我爸的咆哮,和我妈的哭声。
我家的院门大开着,门口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拨开人群,走了进去。
院子当中,站着三个人。
村长林老拴,他老婆,还有水泥厂的王老板。
林老拴的脸黑得像锅底,眼睛里冒着火。
王老板则是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我爸拄着拐,一条腿打着石膏,另一条腿在发抖,脸色苍白。
我妈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捶着自己的胸口。
“你个小!你还敢回来!”
林老拴看见我,一个箭步冲上来,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没躲。
我知道,这一巴掌,我必须挨。
“啪”的一声脆响。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耳朵里嗡嗡作响,嘴里一股血腥味。
“爸!”
一个声音从屋里传来。
林晚秋冲了出来,挡在我面前。
“不关他的事!是我!是我自愿的!”她哭着喊。
“你给我滚回去!”林老拴指着她,气得浑身发抖,“我没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林大哥!林大哥!消消气,消消气!”我妈爬过来,抱住林老拴的腿,“孩子小,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不懂事?”林老拴一脚踹开我妈,“他都敢拐我女儿了,还叫不懂事?陈老三,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
我爸气得嘴唇发紫,想说话,却一口气没上来,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扶住我爸,看着林老拴,一字一句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
“好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王老板终于开口了,阴阳怪气地说,“小伙子,有种啊。就是不知道,你当得起吗?”
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的轻蔑和鄙夷,像针一样扎人。
“王老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说。
“怎么跟我没关系?”他笑了起来,“我本来都快成晚秋的公公了,你半路给我截了胡,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王建军配不上晚秋。”我冷冷地说。
“配不上?”王老板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我儿子配不上,难道你这个泥腿子就配得上了?”
“你家有什么?这三间破瓦房?还是地里那几颗烂西瓜?”
“你拿什么养活晚秋?拿什么给她未来?”
他每说一句,周围村民的议论声就大一分。
我爸的头垂得更低了。
我妈的哭声更响了。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我……”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是啊,我拿什么?
我有什么?
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个高考落榜的失败者。
“说不出来了吧?”王老板得意地笑了起来,“小子,别做白日梦了。你和晚秋,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林村长,”他转向林老拴,“我看这事儿也好办。让这小子拿点钱出来,给晚秋打胎,然后让他滚出村子,永远别回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我们两家的亲事,照旧。”
“不行!”林晚秋尖叫起来,“我死也不嫁给王建军!孩子我生下来!我就跟陈默过!”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我。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神那么决绝,那么疯狂。
我知道,我们俩,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
“好!好!好!”林老拴怒极反笑,“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为了这么个玩意儿,连脸都不要了!”
他指着我,对我爸说:“陈老三,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要么,让你儿子滚蛋,这事儿我既往不咎。要么,就准备给你儿子收尸!”
说完,他拉着他老婆,拽着还在哭喊的林晚秋,气冲冲地走了。
王老板也跟着走了,走之前,还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一地鸡毛。
村民们也觉得没戏看了,三三两两地散了。
我爸一句话没说,拄着拐,默默地回了屋。
我妈坐在地上,还在哭。
“妈,别哭了。”我走过去,想扶她起来。
她一把推开我,哭着骂道:“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啊!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你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你拿什么负责啊?我们家连给你爸看病的钱都快没了啊!”
“林老拴和那个王老板,哪个是好惹的?他们会要了你的命啊!”
我妈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我跪在她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叫进了他的房间。
他坐在床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
我们爷俩沉默了很久。
“你想好了?”他先开了口,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
“不后悔?”
我摇摇头。
他叹了口气,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有大有小,还有一堆毛票。
“这里有三千块钱。”他说,“是你妈攒下来,准备给我换药的。”
“你拿着,明天天一亮,就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爸……”
“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他别过头,不看我,“家里有我,你别担心。”
“我不走!”我哽咽着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我们死不了。”他猛吸了一口烟,“你留下来,才是死路一条。”
“你还年轻,有文化,出去闯一闯,总有出头的一天。”
“至于晚秋那丫头……”他顿了顿,“是我们陈家对不起她。以后你要是出息了,就补偿她吧。”
我跪在地上,抱着我爸的腿,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这是我爸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用他看病的救命钱,给我换一条活路。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天还没亮,我就背上我妈给我准备的干粮和那三千块钱,离开了家。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
我只是不停地走,坐最慢的绿皮火车,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
我在南方一个工地上找了份活,搬砖,扛水泥。
每天累得像条死狗,但晚上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我却睡得格外踏实。
因为我知道,我活着,我得挣钱。
我要把我爸的救命钱挣回来,我要把欠林晚秋的还上。
我断了和家里的一切联系,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林老拴和王建军会通过我,找到我爸妈的麻烦。
每个月,我都会匿名往家里寄钱。
不多,但那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工地的日子很苦,工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唯一的娱乐就是晚上喝点小酒,吹牛打屁。
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女人。
每次听到他们用污言秽语谈论女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林晚秋。
想起她那天晚上,在瓜棚里,那双绝望又倔强的眼睛。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孩子……打掉了吗?
她有没有嫁给王建军?
她……过得好吗?
这些问题,像毒蛇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
但我不敢去打听。
我只能把这些思念和愧疚,深深地埋在心底,变成我搬砖扛水泥的力气。
两年后,我攒了一万块钱。
我离开了工地,在一个城中村租了个小单间,报了个高考复读班。
白天上课,晚上去大排档洗盘子。
那段日子比在工地上还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因为我的心里,有了一束光。
是林晚秋点燃的。
是她让我知道,人不能认命。
越是被踩在泥里,越要仰望星空。
第二年,我考上了。
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只是一个普通的二本。
但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哭了。
我一个人,在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去了。
我终于,有了一点点面对过去的勇气。
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时隔三年,我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但感觉一切都变了。
我家门口新修了水泥路。
我家的三间破瓦房,也翻新成了两层小楼。
我站在家门口,近乡情怯,竟然不敢进去。
“小默?”
一个试探的声音传来。
我回头,看见邻居张大娘,提着个菜篮子。
她愣愣地看着我,看了好半天,才敢认。
“哎呀!真是小默!你可算回来了!”
张大娘这一嗓子,把我妈给喊了出来。
我妈看着我,先是愣住,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冲过来,抱着我,又打又骂。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啊!你这三年死哪儿去了啊!你知不知道妈多想你啊!”
我抱着我妈,任由她的拳头落在我的背上。
“妈,我回来了。”
我爸也拄着拐杖出来了。
他的腿还是没好利索,但气色比三年前好多了。
他看着我,眼圈红了,嘴上却说:“回来就回来,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又坐在一起吃饭了。
饭桌上,我妈跟我说了这三年的事。
我走后,林老拴和王老板确实来找过几次麻烦。
但我爸把那三千块钱拿了出来,说是我留给晚秋的“补偿”,还说我已经死在外面了。
他们闹了几次,没占到便宜,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晚秋呢?”我小心翼翼地问出了那个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妈叹了口气。
“那丫头,也是个烈性子。”
原来,在我走后,林晚秋就以死相逼,死活不肯打掉“孩子”。
林老拴拿她没办法,又怕事情闹大,丢了官位,就把她关在家里。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她就从家里跑了。
也走了。
“走了?”我的心一沉,“去哪了?”
“不知道。”我妈摇摇头,“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她爸妈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有人说她去南方打工了,也有人说她……想不开,跳河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那……王建军呢?”
“他?”我妈撇撇嘴,“他后来娶了镇上另一个厂长的女儿,日子过得挺逍遥。不过前年,他爸的水泥厂出了事,污染太严重,被人举报了,罚了一大笔钱,厂子也关了。他现在就是个混日子的,啥也不是。”
善恶终有报。
我心里没有半分快意,只有一片茫然。
晚秋,你到底在哪?
你过得好不好?
大学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拼命打工。
我拿了所有能拿的奖学金,做了所有能做的兼职。
我没有谈恋爱,也没有什么朋友。
我的心里,只装着两件事:挣钱,和找到林晚秋。
我利用寒暑假,去了很多地方。
广州,深圳,东莞……
所有传说中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我都去找过。
我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张望,在拥挤的工业区打听。
但中国太大了,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
毕业后,我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
996是常态,头发掉得比挣得还快。
但我不敢停下来。
我每个月都给我爸妈寄钱,让他们不要再下地了,好好养老。
我用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写了一个小程序。
一个基于人脸识别的寻人程序。
我把林晚秋唯一的一张高中毕业照,扫描了进去。
然后,我把它挂在了网上,连接了所有我能连接到的公共数据库。
我知道这希望渺茫,甚至有点违法。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像一个偏执的疯子,每天都要打开那个程序几十遍。
看着屏幕上“匹配度0%”的结果,从希望,到失望,再到麻木。
就这么过了两年。
我已经28岁了。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城市大龄未婚男青年。
我妈开始疯狂地给我安排相亲。
“小默啊,你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你看人家张大娘的孙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每次都敷衍过去。
我知道,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叫林晚秋的姑娘。
她不走,谁也住不进来。
那天,我又加完一个通宵的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像往常一样,我习惯性地打开了那个寻人程序。
突然,屏幕上跳出了一个红色的提示框。
“发现高度相似目标,匹配度93.7%。”
我的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手抖得连鼠标都握不住。
照片的来源,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新闻图。
地点,在西部一个偏远的山区。
照片上,一个穿着朴素冲锋衣的短发女人,正蹲在地上,给一个满脸泥垢的小女孩擦脸。
她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虽然她剪了短发,皮肤也晒黑了,脸颊上还有些高原红。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林晚秋。
我像个傻子一样,看着那张照片,又哭又笑。
眼泪把屏幕都打湿了。
她还活着。
她过得很好。
这就够了。
我立刻请了年假,买了去那个山区的机票。
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去。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火车、再到颠簸的盘山公路,我终于来到了那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庄。
村子很穷,比我们村当年还穷。
我按照新闻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支教点”。
其实就是一间破败的土屋。
我到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
林晚秋站在一块用木炭涂黑的木板前,正在教孩子们念拼音。
“a…o…e…”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我没有进去,就站在窗外,静静地看着。
阳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绝望无助的少女了。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和温柔的力量。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她已经找到了她的世界,她的价值。
而我,只是她过去的一个符号。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来这里,到底对不对。
下课铃响了。
孩子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从教室里飞了出来。
林晚秋收拾着教案,一抬头,看见了窗外的我。
她愣住了。
手里的粉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们俩,隔着一扇破旧的木窗,遥遥相望。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夏天的瓜棚。
她慢慢地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陈默?”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
“是我。”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她也笑了,眼圈却红了。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写的程序。”
“程序?”
“说来话长。”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那么傻傻地站着,笑着。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
“我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了。”她说,“当年我从家里跑出来,没地方去,被一个公益组织收留了。后来就跟着他们,到处跑。”
“这里需要老师,我就留下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我知道,这背后,有多少的艰辛和不易。
“你爸妈……”
“我前年回去过一次。”她说,“我爸老了很多,也不再提当年的事了。我妈抱着我哭了一场。”
“他……没当上那个站长。”她补充了一句,语气里听不出是嘲讽还是别的。
“我知道。”
“你呢?”她看着我,“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我说,“我考上大学了,现在在城里当程序员。”
“哦。”她点点头,“那就好。”
又是一阵沉默。
尴尬的沉默。
“那个……”我鼓起勇气,问出了那个埋藏在心底十年的问题,“你……一个人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摇了摇头,笑了。
“不是。”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我不是一个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还有一整个班的学生。”
我看着她狡黠的笑容,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我忍不住也笑了。
“你学坏了,林晚秋。”
“跟你学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村里唯一的小卖部,买了两瓶啤酒,几包花生米。
坐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满天的星星。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这几年的颠沛流离,聊她这几年的支教生活。
聊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截然不同的现在。
“陈默,”她忽然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年,没有真的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看着她,她的侧脸在星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如果当年你真的做了,或许我能逃离王建军,但我也会一辈子看不起你,看不起我自己。”
“是你让我知道,反抗,不一定非要用毁灭自己的方式。”
“是你把我推上了另一条路,一条更难走,但更让我心安理得的路。”
我喝了一口啤酒,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
“其实,我也要谢谢你。”我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年,半夜摸进了我的瓜棚。”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现在还在那个瓜棚里,守着几亩西瓜,抱怨着命运不公。”
“是你让我知道,人,不能认命。”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晚的酒,我们喝到很晚。
没有醉,心却很满。
我在那个小山村待了一个星期,那是我的整个年假。
我帮她修了漏雨的屋顶,给孩子们装了新的电灯,用我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教他们认识外面的世界。
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围着我“陈老师”“陈老师”地叫。
林晚秋就在一旁看着,笑得很开心。
离别的那天,她和孩子们一起来送我。
孩子们拉着我的衣角,依依不舍。
“陈老师,你还会回来看我们吗?”
“会的。”我摸着他们的头,“一定会的。”
我上了那辆破旧的班车,林晚秋站在车下,看着我。
车子启动了。
我看着她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跳下车,想留下来。
但我没有。
我知道,我还有我的责任。
我爸妈还在等我。
我的世界,在那个喧嚣的城市里。
而她的世界,在这片宁静的大山里。
回到城市,我又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的心,不再是空的了。
我开始每个月都给那个山区小学寄钱,寄书,寄各种学习用品。
我和林晚秋,也保持着联系。
我们不聊感情,只聊孩子们,聊工作,聊生活中的琐事。
像两个认识了很久很久的老朋友。
第二年春节,我回家过年。
我妈又开始念叨我的婚事。
“小默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我看着我妈,认真地点了点头。
“有。”
“是谁?”我妈眼睛一亮。
“到时候,我带她回来给您看。”
过完年,我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放着年薪几十万的工作不要,要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
我没有解释。
有些事,不需要向别人解释。
我用我这几年的积蓄,加上我写的一些小程序赚的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会。
专门资助山区的贫困教育。
然后,我背上行囊,又一次踏上了去往那个小山村的路。
这次,我没有买返程票。
我到的时候,正是春天。
山里的桃花都开了,漫山遍野,粉红一片。
林晚秋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我没有打扰她,就站在那棵开得最灿烂的桃树下,等她。
她下课后,看到了我,愣住了。
“你……怎么又来了?没上班吗?”
“我辞职了。”我说。
“辞职了?”她一脸震惊。
“嗯。”我点点头,朝她走过去,“林老师,你们这里,还缺老师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丝我看得懂的欣喜。
“缺。”她点点头,“一直都缺。”
“那……你看我行吗?”我笑着问,“虽然我不会教拼音,但我可以教他们编程,教他们英语,教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圈慢慢地红了。
“陈默,你没必要这样的。”她说,“你有你的人生,我……”
“我的人生,我自己决定。”我打断她,“林晚秋,十年前,在瓜棚里,你问我敢不敢。”
“今天,我也想问你一句。”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林晚秋,这锅饭,我们已经用十年的时间,把米淘干净了,把水烧开了。”
“现在,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把它煮熟?”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但这一次,她的脸上,带着笑。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敢。”
那一年,我在瓜棚守夜,一个漂亮的姑娘摸进我的窝棚,说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拒绝了。
十年后,我去了她支教的山村,在桃花树下,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把这锅饭煮熟。
她答应了。
我们的故事,没有开始在那个燥热的夏夜,而是开始在这个温暖的春天。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们只是两个在泥泞里挣扎过的普通人,用十年的时间,各自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然后,在最恰当的时候,再次相遇。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局。
本文标题:女子用头砸西瓜把自己送进医院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31339.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