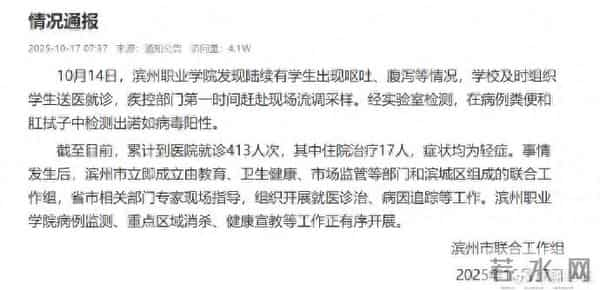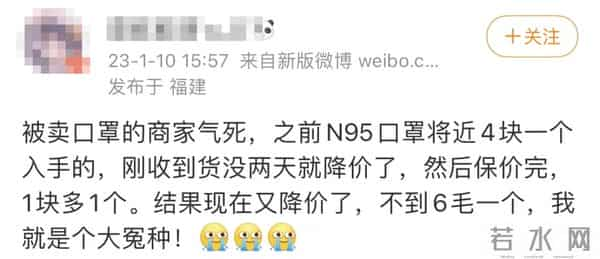紧张到没灵魂的爸爸
凌晨四点半,成都的天,还是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烂麻布。
我叫李伟,一个开了五年滴滴的老师傅。
说“师傅”是抬举自己,其实就是个熬更守夜,拿身体换钱的普通男人。
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震动,是闹钟。
我闭着眼睛,熟练地摸过去,划掉。
身边的老婆美玲翻了个身,嘟囔一句:“吵死了……”
我没吱声,轻手轻脚地爬起来。
客厅里有光,昏黄色的,像风里那点烛火,随时要灭。
是我爸,李建国。
他又起来了。
他坐在那张吱吱呀呀的老藤椅上,身上披着我妈生前给他织的旧毛衣,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那片黑。
这栋老破小的房子,是我妈单位分的。我妈走了十年,这房子就越来越破,像我爸这个人一样。
“爸,你咋又起来了?回屋睡去。”我走过去,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隔壁房间上高三的儿子。
他没反应。
这很正常。
二十九年了,自从二十九年前在工地上被掉下来的钢筋砸了头,他就这样了。
医生说,脑神经严重受损,是痴呆,不可逆。
他活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没有时间,没有记忆,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家。
他有时会笑,对着空气。有时会哭,毫无征兆。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
我给他喂饭,他吃。我给他穿衣,他穿。
他是我爸,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儿子”。
“爸,听见没?回去睡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来看我。
他的眼神,浑浊得像一碗隔夜的米汤。
但今天,就在这碗米汤的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
“伟娃子……”
他开口了。
我的心猛地一抽。
他已经有快十年,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了。平时只会发出一些“啊”、“哦”的单音节。
“欸,爸,我在。”我赶紧蹲下去,凑到他面前。
他盯着我,嘴唇哆哆嗦嗦地动着,好像在用尽全身的力气,从被尘封了二十九年的记忆深井里,打捞几个破碎的词。
“回……回山东……”
山东。
我爸是山东人。这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他的过去。
我是在四川出生的,我妈是四川人。听我妈说,当年我爸是跟着工程队来四川修铁路的,然后认识了我妈,留下了。
“回山东干啥子?”我下意识地用四川话问。
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个破风箱。
然后,一句完整的话,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他干裂的嘴唇里蹦了出来。
“我……我还有个厂子……在山东……”
我愣住了。
厂子?
什么厂子?
我活了四十二年,头一回听说这事。
“爸,你说啥子哦?你喝多了嗦?”我伸手想摸摸他的额头,被他一把打开了。
力气还不小。
“在……淄博……”他又说,眼睛里那点光,更亮了,“张店……我的厂子……”
淄博,张店。
这两个地名,像两颗钉子,瞬间钉进了我的脑子里。
太具体了。
一个痴呆了二十九年的人,不可能编出这么具体的地名。
“爸……”我还想问。
他却好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头一歪,靠在藤椅上,眼睛又闭上了。那点刚刚亮起的光,瞬间熄灭。
他又变回了那尊雕塑。
我站在原地,心脏咚咚咚地跳,像擂鼓。
客厅里死一般地寂静,只有墙上那只老掉牙的石英钟,在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走着。
我看了看我爸,又看了看窗外。
天边,那块烂麻布的边缘,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一个荒唐的念头,像一株疯长的野草,瞬间爬满了我的心。
万一……
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一个痴呆了快三十年的人,说的话能信?
还厂子。
他要真有厂子,我们家至于过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我老婆美玲在服装批发市场当个小销售,一个月累死累活三千多。
我开滴滴,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个七八千,行情不好,刨去油钱保养,也就五千出头。
儿子上高三,补课费、资料费,像个无底洞。
我爸每个月的药费,护理费,又是一大笔。
我们俩的工资,掰成八瓣花都不够。
这个家,就像一辆快要散架的破车,全靠我跟美玲咬着牙,一脚一脚地往前蹬。
现在,我爸,这个家最大的拖累,突然说他在山东有个厂子?
这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
我摇了摇头,想把这个荒唐的念头甩出去。
我扶着我爸回了他的房间,给他盖好被子。
他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我回到客厅,坐在那张藤椅上,我爸刚刚坐过的位置。
椅子上,还留着他的余温。
我点了一根烟。
红星牌的,五块钱一包。抽了好多年了。
烟雾缭绕中,我爸那句话,又在我耳朵边响起来。
“我……我还有个厂子……在山东……淄博,张店……”
那么清晰,那么笃定。
不像是一个痴呆病人说的话。
倒像是一个……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在嘱托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的心,又乱了。
我这辈子,过得挺窝囊的。
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出去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结果呢?
我爸倒下了。
我妈一个人撑不住,我只能留下来。
找了个厂子上班,不高不低的工资,娶了美玲,生了儿子。
后来厂子倒闭,下了岗,没办法,借钱买了这辆车,开始跑滴滴。
我的人生,好像从二十岁开始,就被焊死在了成都这座城市,焊死在了这个破旧的房子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有时候照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两鬓斑白,眼角全是褶子的中年男人,都觉得陌生。
这是我吗?
我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
如果我爸说的是真的呢?
如果山东真的有个厂子呢?
哪怕不是什么大厂子,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小门面……
那也意味着,我的生活,可能会有另一种可能。
我不用再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开着车在大街小巷里转悠,为了几十块钱跟人磨破嘴皮。
我老婆不用再站一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还要看我的脸色。
我儿子,可以上更好的补习班,考一个好点的大学,不用像我一样,一辈子没出息。
这个念头,像一把火,在我心里烧了起来。
越烧越旺。
我知道,这很疯狂。
这简直就是一场赌博。
赌注,是我的时间,我的金钱,还有我那点可怜的希望。
赢了,可能海阔天空。
输了,不过是回到原点,继续我这操蛋的生活。
但是,我已经四十二岁了。
我还能有多少个可以拿来赌的机会?
烟屁股烫到了手,我才回过神来。
天已经大亮了。
美玲已经起床,在厨房里弄早饭,叮叮当当地响。
我做了个决定。
去。
去山东。
去淄博张店。
不管真假,我去看看。
就当是……替我爸,回一次家。
也当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了起来。
“美玲,我跟你商量个事。”
我走进厨房,美玲正打着哈欠下面条。
她眼皮都没抬,“啥事?钱的事免谈,下个月儿子的补课费还没着落呢。”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三句不离钱。
“不是钱的事。”我深吸一口气,“我想……出趟远门。”
“出远门?”她终于抬起头,一脸警惕地看着我,“跑长途啊?去哪?给多少钱?”
“不是跑长途。”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我想去一趟山东。”
“山东?”她皱起了眉头,“你去山东干啥子?我们家有亲戚在那边吗?”
“我爸。”
“你爸?”她更疑惑了,“你爸不是在屋里躺着吗?”
我把凌晨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我说得很慢,很详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我以为,她多少会有点惊讶,或者好奇。
结果,她听完,把手里的筷子往灶台上一拍,发出一声刺耳的响。
“李伟,你是不是疯了?”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愤怒。
“你爸痴呆了多少年了?二十九年!他说的话你也信?他要是说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你是不是也要跑去西边等着?”
“不是,美玲,你听我说,他今天早上……真的很不一样。”
“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他前天还指着电视里的狗喊我名字呢!这叫不一样?”
她的嘴像连珠炮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冒。
“还厂子?他要真有厂子,能眼睁睁看着你妈累死?能眼睁睁看着你开滴滴开得像个鬼一样?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连个好点的补习班都上不起?”
“李伟,你动动你的脑子!你是不是开夜车开糊涂了?”
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她说得都对。
从理智上讲,这事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假的。
但我心里那把火,还没灭。
“万一呢?”我固执地说,“万一那百分之零点一,是真的呢?”
“没有万一!”她吼道,“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吗?去山东,来回车费多少钱?吃住多少钱?你去了,这几天车就跑不了,又少多少钱?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
“你想过个屁!”她气得眼圈都红了,“李伟,我跟你说,你要是敢去,我们就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
离婚。
这两个字,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俩的眼睛里,都充满了疲惫和失望。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想离婚。
她只是太累了,太怕了。
怕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锅里的面条已经煮沸了,白色的泡沫争先恐后地往外冒,像我们俩压抑不住的怒火。
我没再跟她吵。
我知道,吵下去,除了互相伤害,没有任何意义。
我默默地转身,回到房间。
儿子已经去上学了。
我打开衣柜,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一个旧背包里。
然后,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那张我们家仅剩的银行卡。
里面有三万块钱。
是准备给儿子上大学用的,也是我们家最后的救命钱。
我抽出两千块,塞进口袋。
剩下的,我放在了桌子上。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美玲,照顾好爸和儿子。我很快回来。”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背上包,走出房间。
美玲还站在厨房里,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在哭。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对不起。”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句,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一股陈腐的味道。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从成都到淄博,没有直达的火车。
我得先坐到济南,再转车。
绿皮火车,硬座,二十八个小时。
我舍不得买卧铺。
车厢里,一股方便面、汗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我缩在靠窗的角落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
城市,田野,村庄。
一切都变得模糊。
就像我的未来一样。
手机响了。
是美玲。
我犹豫了一下,挂掉了。
很快,短信进来了。
“李伟,你这个龟儿子!你敢走!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感叹号。
我能想象到她发短信时,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了口袋里。
对不起,美玲。
等我。
等我回来。
火车咣当咣当,有节奏地响着。
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地回放过去的片段。
我想起了我爸。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还没出事的时候。
他很高,很壮,肩膀很宽。
他是个木匠,手巧得很。我们家以前的桌子、椅子、柜子,都是他自己做的。
他的手上,总有一股好闻的松木香味。
他话不多,总是闷着头干活。
但他会把我举得很高,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
他的胡茬扎在我的腿上,痒痒的。
我妈总是在旁边笑着骂他:“李建国,你轻点!别把我儿子摔了!”
那时候,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总是充满了笑声。
然后,就是那一天。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
我妈牵着我的手,去工地上给我爸送饭。
我爸在一个脚手架上干活。
他看到我们,冲我们挥了挥手,笑了。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牙齿很白。
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一声巨响,和周围人的尖叫声。
我再看到我爸时,他躺在地上,满头是血。
从那天起,我爸就变了。
他不再笑,不再说话,不再把我举过头顶。
他只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像个木偶。
我妈哭了好久。
后来,她不哭了。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她去菜市场卖过菜,去餐厅洗过碗,去给人家当过保姆。
她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了下去。
她很少跟我提我爸以前的事,也很少提山东。
好像那是她心里的一个禁区。
我只知道,我爸是山东淄博人。
其他的,一概不知。
我妈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伟娃子,你爸……苦啊……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我答应了。
我做到了。
我照顾了他十年。
可是,我照顾的,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真正的李建国,那个会做木工,会把我举过头顶的山东男人,去哪了?
他真的,在淄博,有一个厂子吗?
那个厂子,和他当年的意外,有关系吗?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脏。
二十八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饿了,就啃几口包里带的干面包。
渴了,就接点火车上那带着铁锈味的热水。
周围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他们聊天,打牌,吃东西,睡觉。
整个车厢里,只有我,像个局外人。
终于,广播里响起了“济南站”的提示音。
我背着包,随着人流挤下火车。
一股不同于成都的,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
这就是山东。
我爸的故乡。
我没有停留,直接买了去淄博的火车票。
又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下午三点,我终于站在了淄博的土地上。
我看着“淄博站”三个大字,心里五味杂陈。
爸,我来了。
你的厂子,到底在哪?
我爸只说了“张店”。
张店是淄博的一个区,很大。
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找一个二十九年前可能存在的“厂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能依靠的,只有一个名字:李建国。
我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六十块钱,没有窗户,一股霉味。
但我不在乎。
我把包放下,就出门了。
第一站,张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我想,如果真的有厂子,总该有注册信息吧?
工商局的大厅里,人来人往。
我取了个号,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
轮到我了,窗口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在涂指甲油。
“你好,我想查个企业信息。”我陪着笑脸。
“叫什么名字?”她头也没抬。
“李建国。”
“哪个‘建’,哪个‘国’?”
“建设的建,国家的国。”
她在电脑上敲了一阵,然后不耐烦地说:“没有。”
“没有?”我心里一沉,“不可能啊,你再仔细看看?”
“都说了没有!”她终于抬起头,白了我一眼,“叫李建国的多了去了,你得有具体的公司名字,或者注册号。”
“我……我没有。”我急了,“就是二十多年前,快三十年前注册的,你能不能查查以前的档案?”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大哥,你开玩笑呢?三十年前?那时候都还是手写档案,早就不知道堆哪个仓库里去了,怎么查?”
“那……那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她挥了挥手,像赶苍蝇一样,“下一个!”
我被后面的人推搡着,离开了窗口。
一股无力感,瞬间席卷了全身。
是啊,三十年了。
时代都变了。
我还想靠一个名字,找到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厂子。
是不是太天真了?
我走出工商局,站在马路边,看着车来车往。
淄博的街道,很宽,很干净。
跟成都那种拥挤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感到一阵茫然。
接下来,该去哪?
派出所?查户籍?
我爸的户口早就迁到四川了。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张店的街上乱转。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路边的烧烤摊开始冒出诱人的香气。
我才想起来,我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我找了个路边摊,点了一份淄博烧烤,一瓶啤酒。
小饼,卷着滋滋冒油的烤肉,再配上一根小葱。
味道,确实不错。
但我吃得没滋没味。
邻桌的几个大哥,喝得正嗨,说着我听不太懂的山东话,声音洪亮。
“老王,你那个厂子,今年效益怎么样?”
“嗨,别提了!半死不活的!”
“比我强!我那个早就关门了!”
厂子。
这个词,又刺激到了我。
我鼓起勇气,端着酒杯走了过去。
“几位大哥,打扰一下,跟你们打听个事。”
其中一个光头大哥看了我一眼,“外地来的?”
“嗯,四川来的。”
“哦,四川,好地方啊!”光头大哥很豪爽,“说吧,啥事?”
“我想找个人,叫李建国。三十年前,也可能是在这边开厂子的。”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光头大哥摇了摇头,“李建国?这名字太普通了。三十年前……太久了,没印象。”
另一个瘦高个说:“三十年前,张店这边厂子可多了去了,国营的,私人的,后来倒了一大片。你光说个名字,不好找啊。”
希望,又破灭了一点。
我谢过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口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干。
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却浇不灭心里的那股燥火。
李伟啊李伟,你就是个。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这来找什么虚无缥缈的厂子。
美玲说得对,我就是疯了。
我拿出手机,开机。
几十个未接来电,全是美玲的。
还有几条微信。
“李伟,你到底在哪?回个电话!”
“儿子问我你去哪了,我怎么说?”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了?”
“只要你现在回来,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就湿了。
我想家了。
想美玲的唠叨,想儿子的笑脸,甚至想我爸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回去吧。
我对自己说。
就当是出来旅游了一趟。
梦,该醒了。
我结了账,准备回旅馆,买明天的火车票。
就在我转身的时候,那个烧烤摊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叫住了我。
“小伙子,你等一下。”
我回头,不解地看着他。
“你刚才,是不是在找一个叫李建国的人?”他问。
“是啊,大叔,你认识?”我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
“我不认识。”他摇了摇头,“但是,你说的三十年前,在张店开厂子……我想起个事。”
“什么事?”我急忙问。
“那时候,南边有个‘八陡’镇,那边以前有很多小窑厂,小作坊。后来都关停了。我记得,好像听人说过,有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在那边弄过一个什么东西,手艺特别好。”
“外地来的?手艺好?”我心跳开始加速。
“对,好像……好像也是姓李。”大叔努力回忆着,“不过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清了。你可以去那边问问,那边老住户多。”
八陡镇。
这三个字,像黑夜里的一盏灯,重新照亮了我的路。
“谢谢你!大叔!太谢谢你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嗨,没事,我也是瞎说的,不一定准。”大叔憨厚地笑了笑。
我掏出钱,想再买点什么感谢他。
他摆了摆手,“不用了,快去找吧。”
我冲他鞠了个躬,然后,转身就跑。
我甚至都不知道八陡镇在哪,怎么去。
但我不管了。
只要有线索,我就要去试试。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不能放弃。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去八陡镇的公交车。
那是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小镇,坐车摇摇晃晃一个多小时才到。
下了车,一股煤灰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里,和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干净整洁的张店市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街道很窄,两边的房子都很旧,很多墙皮都脱落了。
路上没什么年轻人,大多是些老人,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晒太阳。
这里,时间好像都走得慢一些。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我地毯式的搜索。
我从街头走到街尾,见人就问。
“大爷,你好,跟你打听个人。”
“阿姨,麻烦问一下。”
“你知道一个叫李建国的人吗?三十年前在这边开过厂子。”
大多数人,都用一种看一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摇摇头。
“没听过。”
“不知道。”
“三十年?小伙子,你记错了吧?”
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嘴皮子都磨干了。
得到的,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失望。
太阳升到了头顶,又慢慢西斜。
我几乎问遍了镇上所有我能看到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李建国。
我累得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脚下那双已经沾满灰尘的鞋。
绝望,像潮水一样,慢慢将我淹没。
我真的,错了吗?
我爸他,只是在说胡话。
而我,就是那个把胡话当真理的傻子。
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我面前走过。
我鬼使神差地,又站了起来。
“大爷,等一下!”
这是我今天问的,不知道第几十个人了。
我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老大爷停下来,眯着眼睛看我。他的耳朵好像不太好。
“小伙子,你叫我?”
“是的大爷,”我凑到他耳边,大声说,“我想找个人!叫李建国!三十年前!在这边开厂子的!”
老大爷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李……建国?”他咂摸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您……您想起来了?”
“你让我想想……”他用拐杖敲了敲地面,闭上眼睛,好像在搜索遥远的记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终于,他睁开了眼睛。
“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
我差点当场跳起来!
“他……他是个外地人,好像是……四川的?”老大爷问。
不对,我爸是山东人,我妈才是四川的。可能他记混了。
“对对对!就是他!”我赶紧点头,“大爷,那您知道他的厂子在哪吗?”
“厂子?”老大爷笑了,露出一口黄牙,“那算不上什么厂子。”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小院子,他租下来,在里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东西。”
“鼓捣什么?”
“木头。”老大爷说,“他是个木匠,手艺好得很!我们都叫他‘小李木匠’。”
小李木匠!
这个称呼,和我记忆里那个会做桌椅板凳的父亲,重合了!
“那……那个院子,现在还在吗?”我颤抖着问。
“在啊,怎么不在。”老大爷用拐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就在那条巷子最里头,一个破院子。他走了以后,就一直荒着了。”
“他……他走了?”
“是啊,”老大爷叹了口气,“好像是二十多年前吧,有一天突然就没影了。听说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回老家了。可惜了,那么好的手艺。”
二十多年前……
时间对上了!
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谢谢您!大爷!太谢谢您了!”
我语无伦次地道着谢,然后,朝着那条小巷,飞奔而去。
那是一条很窄,很深的巷子。
两边的墙上,长满了青苔。
脚下是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
我跑得很快,心脏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巷子的尽头,果然有一个院子。
院门是两扇破旧的木门,上面的红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腐朽的木头。
一把大大的铁锁,挂在门上,已经锈迹斑斑。
就是这里了。
我爸的“厂子”。
我站在门口,喘着粗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激动,紧张,期待,又有一丝害怕。
害怕门后面,是更大的失望。
我伸手,推了推那扇门。
门,纹丝不动。
锁得太死了。
我看了看四周,墙不高。
我退后几步,一个助跑,扒住墙头,翻了进去。
落地的时候,脚下踩起一片尘土。
院子不大,杂草丛生,几乎没人高。
正对着我的,是一排三间瓦房。
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半,另一半也布满了灰尘。
一切,都显得那么破败,荒凉。
这就是我爸的厂子?
我心里的火,凉了半截。
这哪里是什么厂子,分明就是一个废弃的农家院。
我推开中间那间房的门。
门轴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吱呀”声。
一股浓重的灰尘和木屑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挥了挥手,等灰尘散去一些,才看清了屋里的景象。
然后,我就愣在了原地。
屋子不大。
但里面,满满当当,全都是木头。
靠墙堆着一摞一摞的木料,有松木,有柏木,有槐木。
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木屑和刨花。
屋子正中间,摆着一个巨大的木工台。
台子上,各种工具,凿子、刨子、锯子、墨斗……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
虽然落满了灰尘,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主人,是多么爱惜它们。
这……这是一个木工房。
我爸的木工房。
我慢慢地走进去,脚踩在木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走到那个木工台前。
台子上,还放着一个没有完工的东西。
那是一个……小木马。
马的身体已经成型了,线条流畅,打磨得很光滑。
只是马的头,还没有雕刻。
旁边,放着一把刻刀。
好像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马上就会回来,继续他的工作。
我的手,抚摸着那个小木马。
冰凉的,光滑的。
我能想象到,二十九年前,我爸,那个年轻的“小李木匠”,站在这里,拿着刻刀,专注地雕刻着这个木马的样子。
他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是充满希望的,还是带着一丝疲惫?
我的目光,被木工台角落里的一个东西吸引了。
那是一个木箱子。
也很旧了,上面同样落满了灰尘。
我走过去,吹开灰尘,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面,没有金银财宝。
只有一堆……小玩意儿。
全都是木头做的。
有小小的木头汽车,轮子还能转。
有可以拉线的小鸟,翅膀还能扇动。
有小小的拨浪鼓,还有七巧板,鲁班锁……
每一个,都做得那么精致,那么用心。
我拿起那辆小汽车,放在手心。
我仿佛能感觉到,当年我爸在制作它的时候,指尖的温度。
在箱子的最底下,我发现了一个本子。
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已经很旧了,纸张都泛黄了。
我翻开了第一页。
一行隽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
“我的工厂,我的梦想。”
下面,是日期。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二日。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这,是我爸的日记。
“今天,终于租下了这个小院。虽然破了点,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建起我的玩具王国。我的厂,就叫‘伟伟玩具厂’。”
伟伟……
我的小名。
“今天进了第一批木料,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媳妇有点不高兴,但我知道,她心里是支持我的。等我成功了,一定让她过上好日子。”
“伟娃子快一岁了,我给他做了个拨浪鼓。他抓在手里,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看到他笑,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设计了新的图纸,一款可以变形的木头金刚。有点复杂,但我一定能做出来。等伟娃子长大了,肯定会喜欢。”
“隔壁的王大爷说,我做的这些东西,拿去卖,肯定有人买。我有点心动。是不是可以先做一批,去市里试试?”
“今天去市里了,摆了个小摊。卖得不好。城里人都喜欢那些塑料的,电动的玩具。他们不懂,木头的玩具,才有灵魂。”
“有点灰心。但是,我不能放弃。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为了伟娃子。”
“今天接了个私活,去一个工地做木工。能挣点快钱,给媳妇买件新衣服,也给我的‘厂子’增加点经费。”
“工地上的活儿,又脏又累。但是一想到我的玩具王国,我就浑身是劲。”
“媳妇说,让我别太累了。我说,我不累。男人嘛,就该为老婆孩子撑起一片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去工地了。拿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做我的玩具了。我给伟娃子做的小木马,还差个马头没刻完。等我回来,就把它完成。”
“我的‘伟伟玩具厂’,就要正式开业了!”
……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
我记得这个日子。
这是我爸出事的那一天。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了一片墨迹。
原来……
原来这就是我爸的“厂子”。
它不生产机器,不生产钢铁。
它生产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全部的爱和梦想。
他不是一个痴呆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他是一个梦想家。
一个被现实,被一场意外,打碎了梦想的男人。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小院里,寄托在了这些小小的木头玩具上。
他给他的厂子,起了我的名字。
他想为我,建造一个玩具王国。
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二十九年来,我甚至……有点怨他。
怨他成了我的拖累,怨他毁了我的生活。
我真是个混蛋!
我抱着那个笔记本,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被我遗忘的,关于父亲的温暖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他宽厚的肩膀,他手上的松木香,他把我举过头顶时爽朗的笑声……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那个小院里,待了很久很久。
我把每一个木头玩具,都拿在手里,仔细地看。
我仿佛能看到,我爸当年,坐在这里,一刀一刀,雕刻它们的样子。
他的眼神,一定是专注的,温柔的。
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
天,又黑了。
我把那本笔记本,和箱子里那辆小小的木头汽车,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的背包。
至于那个没有完成的小木马,我让它留在了那里。
或许,这是我爸留给自己的一个念想。
我没有再翻墙出去。
我走到门口,看着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锁。
我退后几步,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脚踹了过去。
“哐当”一声巨响。
锁没开,门板倒是被我踹出了一个大洞。
木头,已经朽了。
就像这段被尘封了二十九年的记忆。
我从那个洞里钻了出去,没有回头。
我给美玲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李伟?”她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嗯,是我。”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是沙哑得厉害。
“你……你这个死人!你跑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我快急死了!”她在那头,带着哭腔骂道。
我没有反驳。
“美玲,”我说,“我找到爸的厂子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我明天回来。”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然后就挂了电话。
回去的路上,我还是坐的硬座。
车厢里,依旧是那股熟悉的,混杂着各种味道的气味。
但我不再觉得烦躁。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的手里,紧紧攥着那辆小小的木头汽车。
它的轮廓,在黑暗中,显得那么清晰。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爸,在那个凌晨,突然的清醒,不是偶然。
他或许是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把他心里埋藏最深的秘密,告诉了我。
他不是要我来继承什么财产。
他是要我来,看一看他的梦想。
他要我知道,他曾经,也是一个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爱我的父亲。
他怕我忘了他。
怕我只记得他痴呆后的样子。
回到成都,是第三天的下午。
我走出火车站,阳光有点刺眼。
我打了个车,直接回家。
打开门,家里很安静。
美玲坐在沙发上,看到我,站了起来。
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我们俩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
我走过去,从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和那辆小木头汽车,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这是什么?”她问。
“爸的厂子。”我说。
她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开了。
看着看着,她的手开始发抖。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抱着那个笔记本,无声地哭泣。
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了她。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她把头埋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子……你这个大傻子……”
我知道,她懂了。
她也懂了我的父亲。
晚上,我走进我爸的房间。
他还是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又变回了那个没有灵魂的雕塑。
我坐在他的床边,就像我过去十年里,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我拿出那辆小小的木头汽车,轻轻地,放进了他的手里。
他的手指,很僵硬。
我帮他,一根一根地,合拢,握住那辆小车。
“爸,”我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我回来了。”
“从山东回来的。”
“你的厂子……我看到了。”
“很好。”
“真的,很好。”
“你的手艺,没有忘。大家都还记得你,‘小李木匠’。”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眼睛,依旧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我有点失望,但又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那一次清醒,或许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我帮他把被子盖好,准备离开。
就在我起身的那一刻。
我看到,他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然后,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
“……好……”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
我猛地回头。
他还是那个姿势,那个表情。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
但是,他握着那辆小木头汽车的手,却收紧了。
紧紧地,握住了。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
看了很久,很久。
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我知道,我的生活,不会因为这次山东之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明天,可能还是要凌晨四点半起床,去开我的滴滴。
美玲,还是要回到那个嘈杂的批发市场,去站上一整天。
儿子的补课费,依然没有着落。
这个家,还是那辆吱吱呀呀的破车。
但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的心里,那块空了很久的地方,被填满了。
我不再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疲惫的中年男人。
我是一个梦想家的儿子。
我的父亲,叫李建国。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木匠。
他曾经,想为我,建造一个玩具王国。
而现在,轮到我了。
轮到我,为我的家人,撑起一片天。
我走出房间,轻轻地带上门。
美玲已经做好了晚饭。
很简单的三菜一汤。
“吃饭了。”她说,声音有点沙哑,但很温柔。
“欸,来了。”
我走过去,在餐桌边坐下。
儿子也从房间里出来了,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美玲,好像感觉到了气氛有点不一样。
“爸,你出差回来了?”
“嗯,回来了。”我笑着,给他夹了一筷子他最爱吃的红烧肉。
“快吃吧,吃完了,有力气好好学习。”
“哦。”
我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安安静静地吃着饭。
灯光,很暖。
饭菜,很香。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爸,当年最想要的幸福。
本文标题:紧张到没灵魂的爸爸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35771.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