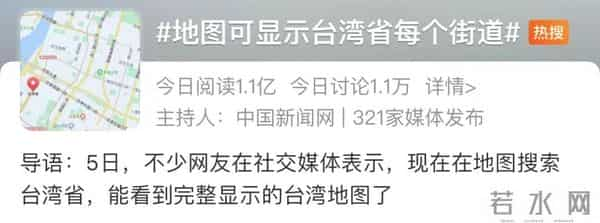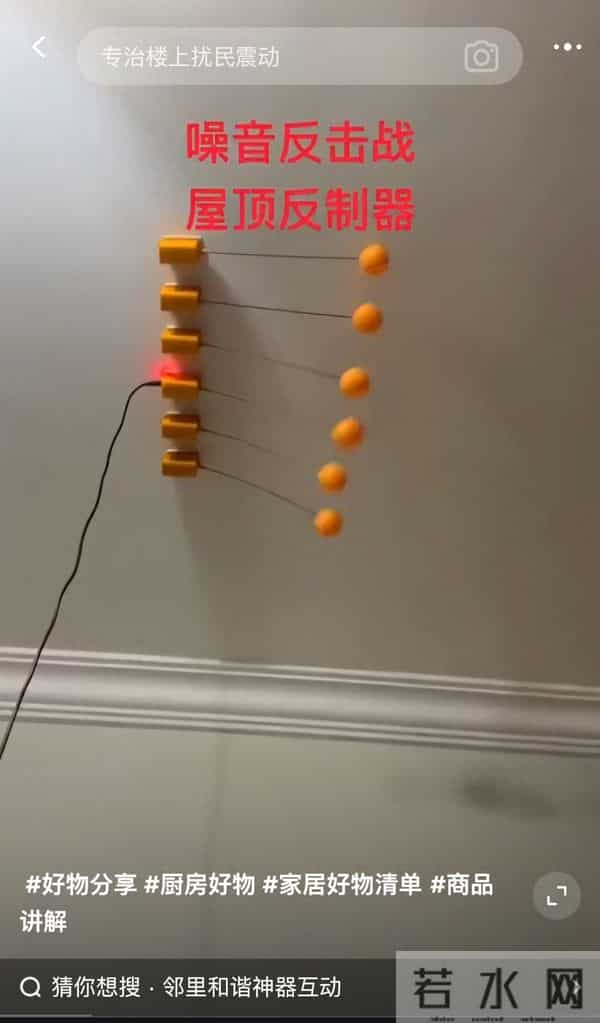忘记28年房子现住户已搬家
我爹失忆了二十六年。
或者说,我们全家都习惯了他失忆的样子。
他叫陈东生,这是我妈给他起的名字。
我妈说,捡到他那天,天刚蒙蒙亮,东方升起一抹鱼肚白,就叫东生吧。
那时候我六岁,我妹陈兰三岁。
我们眼里的爹,就是个整天乐呵呵,但眼神有点飘忽的男人。他会用粗糙的手给我们编草蜢,会扛着我们在田埂上疯跑,但你问他昨天吃了啥,他得歪着头想半天。
村里人都说我妈傻,捡个傻子当男人。
我妈只是笑,用毛巾擦掉他脸上的泥,说,傻点好,踏实。
他就这么踏实了二十六年。
我妈走了十年了,他跟着我过。我开了个小五金店,娶了媳rich,生了个儿子,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磨。
我爹,陈东生,也从一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眼神更浑浊的老头。
我们都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那天下午。
店里没什么生意,我陪我爹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放一个上海的纪录片,东方明珠,金茂大厦,黄浦江上的轮船拉着长长的汽笛。
我昏昏欲睡,我爹却看得格外认真。
他的背,几十年没这么直过了。
突然,他指着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某个老旧弄堂,嘴唇哆嗦着,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一句标准的、带着糯米味的上海话。
“迭个地方,我晓得的……阿拉屋里厢,就勒附近。”(这个地方,我知道的……我们家,就在附近。)
我一个激灵,瞌睡全没了。
“爸,你说啥?”
他没理我,眼睛死死盯着屏幕,浑浊的眼睛里,好像有光。
“我叫李文彬。”
他又说。
这次是普通话,但腔调很怪,跟我听了几十年的那个爹,完全不一样。
“我不叫陈东生,我叫李文彬。我在上海,有套房子。”
我老婆翠萍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听到这话,手一抖,盘子差点摔了。
“他爸,你又犯糊涂了?”
我爹猛地回头,眼神锐利得像刀子。
“我没糊涂!我全都想起来了!”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焦躁地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全是些我们听不懂的词。什么“单位分房”、“产权证”、“霞飞路”、“我老婆小云”、“我儿子阿杰”……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闷棍。
我爹,有老婆?还有个儿子?
那我跟我妹算什么?我那个操劳了一辈子,到死都念着他好的妈,又算什么?
一股无名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别他妈瞎说了!”我吼了一声。
我很少对我爹这么大声说话。
他被我吼得一愣,呆呆地看着我,眼神里的那点光,又慢慢散了,变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陈东生。
他嗫嚅着:“阿……阿金,我……”
“你什么你!吃西瓜!”我把翠萍手里的盘子夺过来,重重地砸在茶几上。
红色的瓜汁溅出来,像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翠萍在旁边翻来覆去,最后忍不住说:“阿金,你说……爸说的是真的假的?”
“假的!”我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摁得变了形,“看了个电视就魔怔了,他要是想起来,二十六年,早干嘛去了?”
话是这么说,可我爹下午那个眼神,那句上海话,像烙铁一样,在我脑子里烙下了印。
第二天,我妹陈兰风风火火地来了。
她一进门就抓着我问:“哥!我听嫂子说了,爸是不是想起来啥了?”
我没好气地说:“想起来个屁,癔症了。”
陈兰不信,跑到里屋去看我爹。
我爹正坐在床边发呆,看到陈兰,他眼睛又亮了。
“阿兰,你来啦。”他拉着陈兰的手,急切地说,“阿拉去上海,好伐?阿拉回屋里厢去。”
陈兰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不像我,她感性,从小就觉得我爹可怜。
“爸,你想起啥了?你跟我们说说。”
我爹就开始说,颠三倒四,但比昨天清晰多了。
他说他叫李文彬,是上海一家仪表厂的技术员。一九九八年,他到我们江西邻省出差,遇到了山洪。后面的事,他就记不清了,醒过来就在我们村的河滩上,被我妈捡回了家。
他说他的房子在静安区,一个叫“昌平里”的弄堂,具体门牌号记不清了,但他说他画得出来。
他还说,他老婆叫林晓云,儿子叫李杰。那年他出差的时候,阿杰应该七岁了。
七岁。
比我当时还大一岁。
我靠在门框上,听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荒诞。
像一场劣质的电视剧。
陈兰听完,抓着我的胳膊,眼睛亮得吓人:“哥,我们去上海!”
“去个屁!”我甩开她的手,“你疯了?他说啥你就信啥?来回车票住宿不要钱?我店不要了?你家那摊子事不管了?”
“钱我出!”陈兰咬着牙说,“哥,这是爸一辈子的事!万一是真的呢?你就忍心让他一辈子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
“他现在有什么不好?吃我的喝我的,我亏待他了?”我火气也上来了,“我妈捡他回来,给他一个家,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到头来,他在外面还有家?你对得起我妈吗?!”
“哥!”陈兰哭了,“你怎么能这么想?妈要是还活着,她肯定也支持我们去找!她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爸找回自己是谁!”
我沉默了。
是啊,我妈临死前,还拉着我的手说,阿金,你爸可怜,以后有机会,还是带他去大城市看看,说不定能想起来点什么。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根一根,都像是烦恼丝。
“我再想想。”
我需要冷静。
我跑到镇上唯一一家网吧,开了台机子。
烟雾缭绕,键盘声噼里啪啦。我笨拙地在搜索框里打下“上海仪表厂”。
跳出来一大堆信息。其中有一家“上海第四仪表厂”,八九十年代很有名,后来改制,合并,现在已经没了。
我又搜“上海 静安区 昌平里”。
地图上显示,这个地方早就拆迁了,原地盖起了一栋闪闪发亮的写字楼。
我的心,沉下去一半。
看吧,都是瞎扯。
我又不死心,鬼使神差地搜了“李文彬 上海第四仪表厂”。
屏幕上加载了半天,跳出一条陈旧的论坛帖子,是十年前的。
一个叫“寻找失落的记忆”的怀旧论坛。
有人发帖问:“还有人记得上海四表的李工吗?技术大拿,可惜了。”
下面有人回:“记得啊,李文彬嘛,九八年去江西出差,遇到洪水,人没了。厂里还给他开了追悼会呢。”
“是啊,他老婆孩子也可怜,后来听说搬走了。”
“他人很好的,特别聪明,就是有点清高。”
我盯着那几行字,手脚冰凉。
烟从指间滑落,烫到了我的手,我却感觉不到疼。
李文彬。
九八年。
江西。
洪水。
全都对上了。
我爹,我那个只会嘿嘿傻笑,连一百块钱都数不清的爹,曾经是个叫李文彬的、聪明的、清高的技术大拿。
他真的有另一个家。
我关掉电脑,走出网吧,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一进门,就看到陈兰和我老婆翠萍,正围着我爹,看他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破日历纸的背面画画。
他画得很慢,手抖得厉害,但线条却异常清晰。
那是一个弄堂的平面图。
哪里是入口,哪里有口井,哪家门口有个石狮子,哪家窗台总是摆着一盆茉莉花。
他指着其中一个位置,说:“这里,二楼,就是阿拉屋里厢。”
翠萍和陈兰一脸震惊地看着那张图。
我走过去,拿起那张纸。
我的心,彻底乱了。
“哥,你信了吧?”陈兰仰头看我,眼里全是希冀。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拍在桌上。
“去买明天去上海的火车票。”
“三张。”
去上海的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摇了十几个小时。
我爹很兴奋,像个要去春游的小学生。他趴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
陈兰在旁边陪着他,给他递水,削苹果。
我一个人坐在对面,抽着烟,看着这对“父女”,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这一趟是对是错。
找到了又怎么样?
那边的人,还认他吗?
就算认,他回去了,那我呢?我妹呢?我们这个“家”,算什么?
一个持续了二十六年的错误?
火车上的饭又贵又难吃,我爹却吃得津津有味。他甚至还点评了一句:“没阿拉上海的排骨年糕好吃。”
陈兰笑得不行:“爸,你还记得排骨年糕啥味儿啊?”
“记得,”我爹一脸笃定,“甜咪咪的,有嚼劲。”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这个男人,是谁?
是给我编草蜢的陈东生,还是那个爱吃排ar骨年糕的李文彬?
到了上海南站,我们三个人,像三只误入瓷器店的土拨鼠。
高楼林立,人潮汹涌。
我爹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近乎陶醉的表情。
“回来了。”他轻声说。
我拉着行李,陈兰扶着他,三个人茫然四顾。
“爸,现在去哪?”陈兰问。
“去静安,昌平里。”我爹毫不犹豫。
我拿出手机导航。
“爸,那个地方已经拆了,现在叫恒隆广场。”
我爹脸上的光彩,瞬间黯淡了下去。
他愣愣地看着我手机上的地图,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哥,那怎么办?”陈兰也急了。
我心里叹了口气。就知道会这样。
“先找个地方住下,再想办法。”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墙纸都发霉了。
我爹不在乎,他放下东西,就催着我们:“走,去看看。”
拗不过他,我们只好打车去了静安。
站在那栋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下,我爹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
他的脖子仰成一个僵硬的角度,像一尊望乡的石像。
周围是穿着精致的白领,踩着高跟鞋,步履匆匆。没有人会多看我们这三个土气的乡下人一眼。
“没了……都没了……”他喃喃自语,眼眶红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
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我才是第一次来这里,却好像也跟着他一起失去了什么。
“爸,别难过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陈兰 an 安慰他。
我把他扶到路边的花坛坐下,给他点了根烟。
他夹烟的姿势很生疏,那是陈东生的姿势。
但他吐烟圈的样子,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和优雅,那是李文彬的。
“我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门牌号了……”他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我就记得,我有一张工牌,上面有我的编号……还有一张身份证……都放在一个铁盒子里……”
“铁盒子?”我心里一动。
我记得,我妈有个铁盒子,是她当年的嫁妆,一直锁着。她去世后,那盒子就归我了,我一直扔在床底下,没动过。
难道……
我立刻给翠萍打电话。
“老婆,你记不记得妈那个红色的铁皮嫁妆盒?在我床底下,你找找,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个更小的铁盒子!”
翠萍在那头翻箱倒柜,过了十几分钟,她声音颤抖地说:“找到了……阿金,里面……里面有张身份证,还有个工牌……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李文彬。”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
“地址!看上面的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昌平里,三十七号,二楼。”
我爹在一旁听着,听到这个地址,猛地站了起来。
“对!就是这个地址!三十七号!我想起来了!三十七号!”他激动得满脸通红。
我挂了电话,感觉像在做梦。
线索,就这么接上了。
“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地址是有了,可房子没了啊。”陈兰又喜又忧。
我想了想,说:“去派出所。”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我们去了最近的静安寺派出所。
接待我们的是个年轻的民警,听我们结结巴巴地讲完这个离奇的故事,他脸上写满了“你们是不是在编故事”的表情。
“失踪二十六年?又想起来了?”他上下打量着我爹,“大爷,您这情况,太复杂了。光凭一张过期的身份证,我们没法查啊。”
“警察同志,求求你了,你帮帮忙吧!”陈兰哀求道,“我爸真的很可怜。”
“不是我不帮,”小民警摊摊手,“系统里查‘李文彬’,全上海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而且九八年失踪,档案早就封存了,我们基层派出所没权限查。”
我爹急了,他抓住小民警的胳膊:“同志,我的工号,我还记得我的工号!上海第四仪表厂,我叫李文彬,工号是73521。”
小民警愣了一下。
大概是我爹报工号时那种清晰、笃定的语气,让他产生了一丝动摇。
他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等。”
他转身进了里间。
我和陈兰,还有我爹,三个人坐在冰冷的长椅上,空气里只有我爹粗重的呼吸声。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小民警和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民警一起走了出来。
老民警手里拿着一份泛黄的档案夹。
他走到我们面前,推了推老花镜,仔细地端详着我爹的脸。
“你……是李文彬?”他试探着问。
我爹猛地点头:“是我是我!”
老民警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同情,还有一丝难以置信。
“我姓王,当年就在这一片儿当片警。我对你有印象。”他说,“你家里的事,我们都知道。”
“我家里?”我爹急切地问,“我老婆小云呢?我儿子阿杰呢?他们还好吗?”
老民警沉默了一下,叹了口气。
“李文彬同志,你听我说,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你当年失踪后,被报了死亡。你爱人林晓云,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很不容易。过了几年,大概是零二年的时候,昌平里拆迁,他们拿了笔拆迁款,就搬走了。”
“搬走了?搬去哪里了?”我爹追问。
“我们档案里有记录,他们搬去了浦东的一个小区。”老民警翻开档案,“我看看……叫‘金桥花园’。”
“那他们现在……”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户籍信息是动态的,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搬家,我们这里查不到。不过,”老民警顿了顿,“我们这里有你爱人林晓云当年留下的一个联系电话。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通。”
他把一个手机号码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感觉它有千斤重。
这个号码背后,是另一个家庭。
是我爹真正的家庭。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陈兰已经泣不成声。
我们走出派出所,上海的傍晚,华灯初上,车水马龍。
我爹看着手里的纸条,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打吧。”他看着我,眼里满是恳求。
我拿出我那部用了五年的旧手机,深吸一口气,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
电话响了很久。
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那边接了。
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警惕和不耐烦。
“喂?哪位?”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说话啊?谁啊?再不说话我挂了!”
“请……请问,是林晓云女士家吗?”我终于挤出声音,干涩沙哑。
那边沉默了几秒。
“你找我妈什么事?”
我妈……
这个称呼,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他就是阿杰。
那个我爹念叨了一路的儿子。
“我……我们是……从江西来的。”我语无伦次,“我们想找一下林晓ve女士,关于……关于李文彬的事。”
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
我甚至能听到他瞬间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开口,声音冷得像冰。
“我爸早就死了。你们是什么人?骗子?”
“不是!我们不是骗子!”陈兰在我旁边抢过电话,哭着喊道,“我爸他没死!他就是李文彬!他失忆了二十六年,现在才想起来!我们来上海找你们了!”
那边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是一声冷笑。
“失忆二十六年?你们这故事编得可真好。我凭什么信你们?”
我爹在一旁听着,急得满头大汗,他抢过手机,对着话筒大喊:
“阿杰!是爸爸!我是爸爸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六岁生日,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变形金刚,是擎天柱!你把它藏在床底下,怕被妈妈发现!”
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
只有电流的滋滋声。
又过了许久,那个叫李杰的男人才开口,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
“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一家老字号的茶楼里见的面。
我特意选的,想着环境能缓和一下气氛。
我们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我爹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一杯茶水,洒了大半。
陈兰不停地给他整理衣领,嘴里念叨着:“爸,你别紧张,别紧张。”
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人来人往,心里空落落的。
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马上要观看一场与我无关,却又将深刻改变我人生的戏剧。
一个穿着得体,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头发花白、气质端庄的老太太,走进了茶楼。
男人径直朝我们走来,目光在我、陈兰和我爹脸上扫过。
当他的目光落在我爹脸上时,他停住了脚步。
他身后的老太太,也看到了我爹。
她捂住了嘴,眼睛在一瞬间瞪得老大,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
我爹也站了起来,看着那个老太太,嘴唇哆嗦着,喊了一声:
“小……小云?”
那个叫林晓云的女人,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但她没有冲上来拥抱。
她只是站在原地,任凭眼泪往下流,眼神里有震惊,有悲伤,有怨恨,还有二十六年岁月积攒下来的、我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那个叫李杰的男人,扶住了他摇摇欲坠的母亲。
他看着我爹,眼神冰冷,带着审视。
“你真的是我爸?”他问。
我爹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眼泪也流了下来。
气氛凝固到了极点。
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坐下说吧。”我站起来,给他们拉开椅子。
没人说话。
茶水的热气氤氲上升,模糊了每个人的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杰终于开口,他看着我,似乎把我当成了主事人。
我把我爹如何失忆,如何被我妈捡到,如何在我们家生活了二十六年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林晓云女士一直在哭,用手帕不停地擦着眼泪。
李杰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冰冷,慢慢变得复杂。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看向我爹。
“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爹看着他,又看看林晓云,脸上满是愧疚。
“我……我不记得了。”他说,“我就记得,那天雨很大,山路很滑,车翻了……再醒过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句不记得了,就是二十六年?”李杰的音量陡然提高,情绪有些失控,“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我妈是怎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吗?所有人都说你死了!我们给你立了衣冠冢!每年清明我们都去给你烧纸!结果呢?你他妈在乡下娶妻生子,过得挺快活啊!”
他最后一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不是的!”陈兰激动地站起来,“我爸他不是故意的!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过得一点都不好!他就是个傻子!我们村里人都欺负他!是我妈……是我妈照顾了他一辈子!”
“那你妈呢?”李杰冷冷地看着我们,“现在你爸想起来了,你们就把他送回来了?这是什么?完璧归赵?”
他的话,刻薄又伤人。
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我们没想把他怎么样!”我盯着他,“我们只是想搞清楚真相!我爸念叨着上海有套房,有家人,我们就带他来了!我们没想过要你们一分钱,也没想过要赖上你们!”
“房子?”李杰冷笑一声,“那套房子,为了供我上大学,为了给我妈治病,十几年前就卖了!你们想要的房子,没了!”
我爹听到这话,身子晃了晃,跌坐回椅子上。
他来上海的唯一念想,那个“屋里厢”,没了。
“阿杰,别这么说。”林晓云拉了拉儿子的衣袖,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
她看着我爹,看了很久很久。
“文彬,你老了。”她说。
我爹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小云,我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林晓云摇摇头,她看向李杰,“你对不起的是你儿子。”
她又转头,看向我和陈兰。
“也对不起他们。”
她叹了口气,眼神里是无尽的疲惫。
“你们……跟我回家吧。”
李杰的家,在浦东一个很普通的小区。
三室一厅,装修得很温馨。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的全家福。
年轻的李文彬,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旁边站着笑靥如花的林晓yun。
照片里的李文彬,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意气风发。
和我那个在田埂上打滚的爹,判若两人。
我爹站在那张照片前,伸出手,想要触摸,又缩了回来。
李杰给我们倒了水,态度比在茶楼时缓和了一些。
“你们今晚,就先住在这里吧。”他说,“有一间客房。”
他顿了顿,补充道:“你们三个。”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让他“死而复生”的父亲,立刻融入这个家。
晚上,我和陈兰,还有我爹,挤在小小的客房里。
谁也睡不着。
“哥,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陈兰小声问。
“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来上海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找到了真相,找到了他的家人。
可然后呢?
把他留在这里?
我们转身就走,当这二十六年是一场梦?
我做不到。
我爹,陈东生,是我爸。他养了我二十六年,虽然他脑子不清醒,但他给了我一个父亲能给的所有。
可李文彬,也是他。他亏欠了眼前这个家二十六年。
他像一个被劈成两半的人,一半在江西,一半在上海。
哪一半,都凑不齐一个完整的人生。
“阿金。”
我爹突然开口了。
他坐在床边,背对着我们,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对不起你妈。”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是啊。
这场跨越了二十六年的悲欢离合里,最无辜,最委屈的,是我那个已经长眠地下的母亲。
她用一辈子的善良和辛劳,爱了一个不属于她的男人,支撑起一个本不该存在的家。
到头来,却什么都没留下。
第二天,李杰请了假,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他开着车,沉默地穿过大半个上海。
车停在了一处公墓。
他带着我们,走到一个墓碑前。
墓碑上没有照片,只刻着一行字:
爱夫李文彬之墓。
立碑人:妻林晓云,子李杰。
我爹,不,李文彬,跪倒在墓碑前,嚎啕大哭。
哭得像个孩子。
他抚摸着那冰冷的石头,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李杰站在一旁,眼眶通红,但始终没有掉一滴泪。
我和陈兰站在不远处,像两个闯入者,手足无措。
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气氛依旧压抑。
“我恨过你。”李杰突然开口,他看着后视镜里的李文彬,“我小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爸爸接送,我没有。他们都笑话我是没爹的野孩子。我妈为了我,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你根本不知道。”
“后来我长大了,我开始理解她。她心里一直有你。她一直不肯再嫁,她说,你那么聪明,那么好的人,不可能就这么没了,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我们都绝望了。”
“我们给你立了碑,我们接受了你已经死亡的事实。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想让我妈过上好日子,我想让她忘了你。”
“可是昨天,你突然就出现了。”
李杰把车停在路边,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李文彬。
“你让我怎么办?让我妈怎么办?让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迷茫。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回到家,林晓云做好了一桌子菜。
很丰盛。
有红烧肉,有熏鱼,有油焖笋。
都是地道的上海本帮菜。
她给我爹夹了一块红烧肉。
“你以前最爱吃的。”她说。
我爹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他眼里的泪,又掉了下来。
滴在碗里。
“味道……没变。”他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陈东生正在一点点地消失。
李文bin,正在回来。
那顿饭,所有人都吃得食不知味。
晚上,李杰把我叫到了阳台。
他递给我一根烟。
“谢谢你们。”他突然说。
我愣住了。
“谢谢你们,照顾了他二十六年。”他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他看起来……被照顾得很好。很健康。”
我抽了口烟,吐出烟圈。
“是我妈照顾的他。”我说,“我只是……接了个班。”
我们沉默地抽着烟。
“你们……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反问他:“你们呢,打算怎么办?”
李杰苦笑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妈的意思,是想让他留下来。毕竟,他是我爸。”
“那我们呢?”我脱口而出。
李杰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知道,这对你们不公平。”他说,“你们可以提条件。补偿,或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家能做到的。”
“补偿?”我笑了,笑得有点凄凉,“我妈一辈子的青春,我跟我妹二十六年的父爱,怎么补偿?用钱吗?”
李杰不说话了。
“他是我爸。”我说,一字一句,“不管他叫陈东生,还是叫李文彬,他都是我爸。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那你的意思是?”
“我带他来,是想让他找回自己。现在找到了,该怎么选,是他的事。”我把烟头摁灭在栏杆上,“明天,我们就回江西了。”
“那他呢?”
“你问他自己吧。”
我回到房间,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陈兰和我爹。
陈兰哭了。
我爹愣住了。
“阿金……你不要爸了?”他拉着我的手,像个怕被抛弃的孩子。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看着他,他眼神里的慌乱和依赖,是陈东生的。
“爸,”我说,“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有老婆,有儿子。他们等了你二十六年。”
“可你……你和你妹……还有你妈……”
“我妈已经不在了。”我打断他,“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好好的。现在你好了,你应该回到你原来的生活里去。”
我说得很大义凛然。
其实我的心在滴血。
我像一个偷了别人宝贝二十六年的小偷,现在,物归原主的时间到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买了回程的火车票。
两张。
我和陈兰的。
当我把车票拿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
“哥!你什么意思?”陈兰尖叫起来。
“爸留在这里。”我说。
李文彬看着我,嘴唇颤抖,说不出话。
林晓云和李杰也看着我,眼神里全是震惊。
“这是他应该待的地方。”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我们该回去了。店里还一堆事呢。”
我把我的行李拖到门口。
“哥!”陈兰冲过来,死死拉住我,“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把爸一个人丢在这里?他在这里谁也不认识!他会不习惯的!”
“他有他老婆,有他儿子,怎么会不习惯?”我甩开她的手,“他在这里,是李工,是技术大拿。跟我们回那个小镇子,继续当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傻子吗?”
我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阿金……”李文彬终于开口了,他走到我面前,老泪纵横,“爸跟你回去。”
“你不是我爸。”我看着他,狠下心说,“我爸叫陈东生,他只会嘿嘿傻笑,他一辈子都没出过我们那个镇。你不叫陈东生。”
“我……”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我走了。”我转过身,不敢再看他的眼睛。
我怕我一看,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刚拉开门,李杰突然开口了。
“等一下。”
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
“让他自己选。”他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李文彬身上。
他站在客厅中央,看看我,又看看李杰和林晓云。
他的脸上,满是痛苦的挣扎。
一边,是亏欠了二十六年的妻儿和故乡。
另一边,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相伴了二十六年的养子和“家”。
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就要做出选择。
他抬起头,看着我,又看着李杰。
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他缓缓地,跪了下来。
“爸!”
“文彬!”
我和李杰,林晓云,陈兰,同时惊呼出声。
“我对不起你们。”他跪在地上,泣不成声,“我对不起小云,对不起阿杰……我也对不起阿金他妈,对不起阿金,对不起阿兰……”
“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他像个迷路的孩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彻底崩溃了。
那一刻,我所有的怨恨,所有的不甘,都烟消云散了。
我只觉得心疼。
我走过去,和李杰一起,把他扶了起来。
“爸,你别这样。”我声音沙哑。
“爸,起来。”李杰也开口了,声音里带着哽咽。
我们两个,一个江西的五金店老板,一个上海的白领。
在这一刻,因为同一个男人,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共识。
李文彬,先跟我回江西。
用李杰的话说:“让他先回去适应一下,也让我们……适应一下。”
林晓云没反对,她只是拉着李文彬的手,嘱咐了很久。让他注意身体,按时吃药。
她说,她会和李杰去看他。
离别的时候,在火车站。
林晓云给我和陈兰的包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不要。
她硬是塞了进来。
“这不是给你们的补偿。”她说,眼眶红红的,“这是……这是我替文彬,给你们妈妈的一点心意。我知道她不在了……就给她……多烧点纸吧。”
我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
回去的火车上,李文彬,或者说我爹,一直很沉默。
他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兴奋地看着窗外。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手里攥着林晓un给他的一张照片。
是李杰现在的全家福。
照片上,李杰的妻子笑得很甜,他的女儿,扎着两个小辫子,很可爱。
我知道,他的人生,已经被撕裂了。
他再也回不到那个只会嘿嘿傻笑的陈东生了。
也再也回不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文彬了。
他卡在了中间。
回到家,翠萍看到我们三个都回来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我爹还是住在我家,每天帮我看看店,逗逗我儿子。
但他变了。
他话少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他会教我儿子说几句上海话。
他会看着电视里的财经新闻,跟我讨论几句股票。
他不再是那个纯粹的陈东生了。
镇上的人都知道了我家的奇闻。
他们看我爹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好奇和敬畏。
他们不再叫他“傻子东生”,而是叫他“李工”。
我和李杰,加上了微信。
我们很少聊天,但每隔几天,他会给我发几张他女儿的照片,或者问问我爹的近况。
我也会拍几张我爹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视频发给他。
我们就像两个小心翼翼的“共享父亲”的兄弟,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个月后,李杰和林晓云真的来了。
他们开着车,带了很多上海的特产。
林晓云一看到我爹,眼泪就下来了。
我爹看到他们,也很激动。
我让翠萍做了一桌子我们江西的菜。
饭桌上,林晓云看着我爹,吃着我们这里的辣菜,没有丝毫不适,她轻声说:“文彬,你口味都变了。”
我爹笑了笑:“都好,都好吃。”
那天晚上,我们两家人,坐在我家的那个小院子里。
李杰的女儿,我爹的孙女,和我儿子,我爹的另一个孙子,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林晓云和我老婆翠萍,在厨房里聊着家常。
我和李杰,还有我爹,三个人坐在院子里,喝着酒。
谁也没提以后怎么办。
但我们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李杰说,他想在上海附近,买个小一点的房子,让我爹和林晓云一起住。离他近,方便照顾。
他又看着我,说:“也欢迎你们……随时来住。”
我说,我过阵子,想带我爹,去我妈的坟上看看。
我爹听着,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
我知道,他心里有一杆秤。
这杆秤,倾斜了二十六年,现在,需要慢慢地,一点点地,找回平衡。
这很难。
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回绝对的平衡。
我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我带我爹去上海,站在那栋叫恒隆广场的大楼下。
我们去寻找一套房子。
最后,房子没了。
但我们却找到了两个家。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江西。
一个属于李文彬,一个属于陈东生。
而我爹,就站在这两个家的中间。
他失忆了二十六年,找回了过去。
而我们,却因为他的找回,而陷入了更深的迷惘和联结。
我不知道他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人生里,多了一个叫李杰的“兄弟”。
我爹的人生里,也多了一个叫李文彬的沉重过往。
这一切,都开始于那个平平无奇的下午。
我爹指着电视,说他在上海有套房。
我们赶过去,当场愣住。
我们愣住,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财富。
而是因为命运,在二十六年后,以一种我们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露出了它那张荒诞、残酷,却又带着一丝温情的脸。
本文标题:忘记28年房子现住户已搬家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40614.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