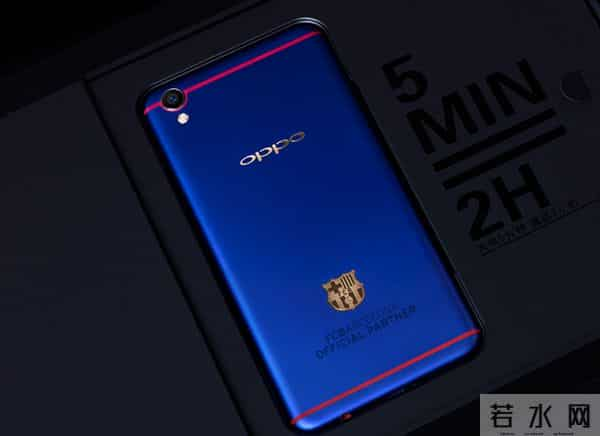梅雨季节是几月到几月
若在往年,这时节的西安,该是另一番光景了。天是那种又高又远的蓝,像一块上好的青金石,澄澈而坚硬;阳光呢,也不再是夏日那般白晃晃的泼辣,变得醇和而温润,照在庙檐的鸱吻上、城墙的方砖上,泛出一种沉静的、蜜色的光。空气里满是干燥爽利的气息,风过处,法桐的叶子沙沙作响,那声音是脆的,干的,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解索之意。可今年,这一切都失了约。九月像是被谁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捞出来时,已是湿漉漉、沉甸甸的十月了。

这雨,下得没有道理,下得让人心慌。它不像北方的夏雨,来时是霹雳弦惊,万鼓齐擂,去时是雨收云散,干脆利落。这雨,是南方的秉性,是黏缠的,暧昧的。它没有声响,或者说,它的声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低沉的背景音,像无数的蚕在啮食着巨大的桑叶,悉悉索索的,填满了天地间所有的空隙。你走在街上,看不见雨丝,只觉得空气是浑浊的,饱含着水汽的,像一团湿冷的棉花,堵在你的口鼻之间。不一会儿,头发上便结了一层细密的白珠,衣裳也渐渐地润了,软塌塌地贴在身上,那种凉意,不刺骨,却丝丝缕缕地,直往骨头缝里钻。
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视线所及,一切都晕开在了一片灰蒙蒙的色调里。远处的楼房,失了往日棱角分明的轮廓,成了水墨画里淡淡的远山。街边的树木,无论是槐是桐,叶子都被这无休无止的雨水泡得发黑,肥腴得有些可怖,沉沉地垂着头。地面上,无一处不是湿的。人行道的方砖,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像一幅未干的水墨。墙角,石阶的缝隙里,不知何时,悄悄地蔓上了一层滑腻的青苔,那绿是幽暗的,饱含着水光的,是这北方城市里不该有的、近乎于妖的生机。

人们的生活,也被这雨水搅得乱了章法。阳台上挂着的衣物,一连几日也干不透,摸上去总带着一股潮润的、微生的气味,逼得人用电热器的暖风,在屋里制造出一小片焦燥的、不自然的“晴空”。家中的物什,木器的接榫处有些松胀了,铁器的表面也浮起星星点点的黄锈。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快要朽坏前的气息。人的心情,也便在这无尽的潮湿与阴冷里,渐渐地发了霉。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只想蜷在屋里,听着那窗外永恒的、淅淅沥沥的声响,那声音里没有安慰,只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温柔的消磨。
这哪里还有半分长安秋天的影子?记忆里的长安秋日,是“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飒爽,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澈。那是一种属于帝王之州的气象,开阔,疏朗,连感伤都是壮阔的。而今这般,倒像是硬生生将江南的梅雨,搬到了这八百里秦川之上,让这座雄浑的北方城池,平添了几分不属于它的、婉约的愁怨。

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在江南客居的时光。那里的梅雨,便是这般黏腻,这般无孔不入。但江南的屋子,自有它的应对,白墙黛瓦,坡顶陡峻,为的就是让雨水快些流走;屋里的地是铺着木板的,底下留有空隙,防的便是这地气的上返。而西安的宅院,却是敦敦实实的,墙厚而窗小,为的是抵御冬日干冷的北风,何曾想过要防备这样缠绵的水汽?这便像一个惯于在沙场上挥砍的关西大汉,忽然被逼着去学绣花,那份窘迫与不适,是刻在骨子里的。
夜深时,雨声似乎更清晰了些。我躺在床上,了无睡意。这雨,下得久了,竟让人生出一种奇异的错觉,仿佛这世界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天穹如盖,从来便是这般灰蒙蒙、湿漉漉的;而那秋高气爽的记忆,倒像是一个遥远而不真切的梦了。
不知这“陕西梅雨”,还要下到何时。也不知这被雨水浸透了的、温柔而憔悴的长安,何时才能找回它那副坚硬、干燥的、属于北方的骨骼。#西安天气##西安生活##西安身边事#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