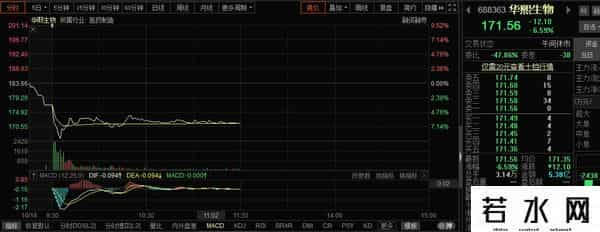年轻的夜,原来人一生要熬的夜,都是年轻时欠下的清醒
凌晨三点二十七分,空调嗡鸣着吐出冷气,却丝毫吹不散我心中的燥热。电子钟幽幽的蓝光,像极了某种不眠的诅咒。汗湿的睡衣粘着皮肤,我徒劳地翻转身体,枕头仿佛塞满了荆棘,每一次呼吸都沉重地拖曳着难以排解的焦灼。黑暗中,手机屏幕猝然亮起,如一道冷冽的闪电劈开了粘稠的夜色。那条消息带着不可思议的陌生又熟悉的气息,刺入我的眼帘:“林晚同学,我是陈旭的父亲,他留在我这里一封信,嘱咐务必在十年后交给你。”
陈旭?这个名字像一个沉睡了许久的古老咒语,此刻骤然苏醒,带着遥远岁月里阳光、汗水与风声的呼啸,猛烈地撞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我几乎是从床上弹了起来,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连指尖都微微发颤。
我跌跌撞撞地扑向书柜最底层,那里尘封着一个褪色的纸盒,里面静静躺着一本同样褪色的硬壳同学录。指尖翻过那些早已泛黄的纸张,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夸张字迹和故作深沉的祝福语,青涩得令人心头发紧。终于,在接近末尾的一页,属于陈旭的那张纸赫然在目。照片上的他咧着嘴,笑容放肆而明亮,几乎要灼痛人的眼睛。目光急切地扫过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在页脚处,一行格格不入的、用黑色记号笔郑重写下的字迹牢牢锁定了我的视线:“林晚,十年后,老地方见。你若不来,我就一直等。——陈旭” 日期,正是那个被汗水浸透的、属于我们十八岁的夏天。
那一年,阳光炽烈得如同熔化的金箔,蝉鸣是唯一的背景音,单调又执拗。高考结束的狂欢如潮水般退去,留下少年人特有的、近乎虚脱的茫然。毕业聚餐那晚,我们一群人从喧闹的KTV里踉跄出来,笑声在夏夜里显得格外空旷。陈旭不知何时推来了他那辆宝贝的二手摩托,黑色的车身在昏黄路灯下闪着幽光。他跨坐上去,动作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流畅与不羁,拍了拍后座,眼睛亮得惊人:“林晚,敢不敢跟我走?” 他的声音被夜风吹得有些飘忽,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挑战命运般的蛊惑。
夜风在耳边猎猎作响,城市的灯火被疾驰的车速拉成模糊的光带。我紧紧环抱着陈旭的腰,隔着薄薄的T恤能清晰感受到他脊背传来的温热和力量,以及少年蓬勃的心跳。他载着我一路狂飙,最终停在城市边缘那座荒废的观景台上。我们并肩坐在冰凉的水泥围栏上,脚下是沉睡的城市,头顶是浩瀚得令人窒息的星河。晚风温柔地撩拨着我们的头发和衣角。他突然侧过脸,眼睛在星光下亮得惊人,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林晚,我们……要不要在一起试试?” 那一刻,夏夜的风仿佛都停止了流动,星河在头顶无声旋转,少年人的莽撞与试探,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无声地蔓延开来,带着令人眩晕的微光。
然而,十八岁的骄傲与莫名的矜持,如同无形的壁垒。我几乎是下意识地、用一种近乎刻薄的语气回应了他:“陈旭,我们这算早恋吗?太幼稚了吧!”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惊愕于那份言不由衷的锋利。他眼底那簇明亮的火苗瞬间黯淡下去,像是被风粗暴地吹熄,只剩下冰冷的灰烬。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都凝固了,才低低地说:“……我知道了。” 那声音轻得仿佛被夜风揉碎。随后几天,我赌气般地刻意回避着他所有的电话和消息,像一只愚蠢的鸵鸟,固执地把头埋进自己用骄傲堆砌的沙丘里。直到某个闷热的午后,我听说陈旭一家突然搬走了,走得无声无息,干净得仿佛从未在这座城市存在过。
我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才拨通了陈旭父亲电话里留下的地址。天光微熹时,我已经站在一栋老旧居民楼下。开门的是位身形瘦削、头发花白的老人,眉宇间依稀能辨认出陈旭当年的轮廓,只是被岁月和某种深重的哀伤冲刷得模糊不清。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递过来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是熟悉的、属于陈旭的飞扬笔迹:“林晚亲启”。
我颤抖着接过信封,那薄薄的分量却像有千钧之重。老人没有让我进门的意思,只是静静地带上了门。我背靠着冰冷的楼道墙壁,指甲深深掐进信封边缘,终于撕开了那道封印了十年的时光裂口。里面只有一张小小的纸条,展开来,上面依旧是陈旭那熟悉到刺眼的字迹,简短得令人心碎:
“林晚,明天见。”
明天见?
这三个字像三根冰冷的钢针,猝然刺入我的心脏,带来一阵尖锐的麻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理解这简单字句背后的含义。就在这茫然失措的瞬间,楼道里那扇紧闭的门竟又无声地滑开了。陈旭的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被漫长时光磨砺出的、近乎冷酷的平静。他看着失魂落魄的我,声音低沉沙哑,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年夏天……他写完这封信,说要出门……去等一个‘明天’。” 老人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砸在我的神经上,“十年前的夏夜,他骑着摩托……撞上了盘山公路的护栏。就在……你们常去的那个观景台下面。”
那一瞬间,我仿佛被无形的巨锤狠狠击中,踉跄着后退一步,脊背重重撞在冰凉的墙壁上。信纸从我骤然失力的指间滑落,像一片毫无重量的枯叶,打着旋儿飘向布满灰尘的水泥地面。我再也支撑不住,顺着粗糙的墙壁滑坐到地上,蜷缩在冰冷阴暗的楼道角落里。没有嚎啕,没有呼喊,只有身体无法抑制的剧烈颤抖,像一片在狂风中被撕扯的落叶。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旋转,耳边只剩下血液冲刷鼓膜的轰鸣,以及老人那几句冰冷话语在灵魂深处反复撞击的回响。十年。原来那个“明天”,早已被永远地凝固在十年前的夏夜里,凝固在盘山公路那扭曲的护栏和刺眼的血痕之中。
我不知是如何走出那栋如同坟墓般的老楼。晨光熹微,城市正在苏醒,街道上渐渐有了行人和车辆的声音,充满了人间烟火的生机。而我,像个被抽离了魂魄的躯壳,手里死死攥着那张已然被揉皱的纸条,漫无目的地走着。那张写着“明天见”的纸条,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灼烧着我的掌心,也灼烧着我迟到了十年的灵魂。
不知不觉,双脚竟像有了自己的意志,将我带到了城市边缘那座废弃的观景台。十年风雨侵蚀,这里愈发破败荒凉。我一步步走上平台,每一步都踩在记忆的碎片上,发出令人心碎的声响。水泥围栏冰冷依旧,只是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埃和枯叶。我伸出手,指尖拂过粗糙冰冷的表面,仿佛还能触摸到那个夏夜残留的温度,触摸到
少年倚靠在这里时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站在陈旭曾经站立的位置,目光投向下方。那条熟悉的盘山公路在晨雾中蜿蜒,护栏在远处某个弯道反射着金属的冷光——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狰狞伤口。
就在那个瞬间,东方天际,云层骤然裂开一道缝隙。一轮无比硕大、无比猩红的朝阳,毫无预兆地、磅礴地跃出地平线,将血一般浓烈的光芒泼洒下来,瞬间浸透了整个荒芜的平台,也浸透了我空洞的躯壳和手中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我迎着那刺眼的光芒,长久地、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一尊被重新浇筑的雕像。那封信,那张纸条,那个凝固在十年前夏夜的“明天”,终于在此刻汇成一股汹涌的洪流,彻底冲垮了我所有的堤防。
灼热的泪水终于决堤,无声地、汹涌地滚落脸颊。原来人一生要熬的夜,都是年轻时欠下的清醒。十年前那个本该无眠的夜晚,我因浅薄的骄傲和懵懂的犹疑,竟昏沉地睡了过去;而十年后这个被真相刺穿的凌晨,我终于彻彻底底地醒来了,却是在一个永远失去“明天”的、血色的黎明。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