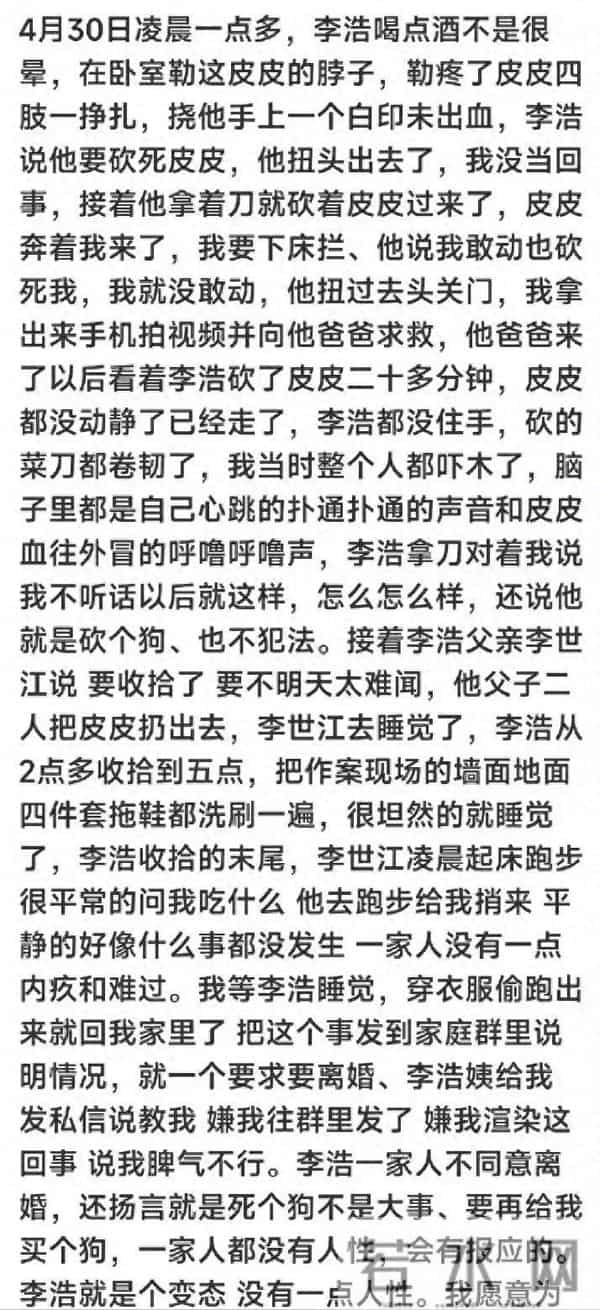妈妈想陪女儿上大学当上食堂阿姨
我叫李娟,在大学食堂打了三十年饭。
我这辈子,一半的喜怒哀乐,都混在那一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里了。
今年五十五,马上退休。
消息是上个月下来的,王主任找我谈的话。
他搓着手,一脸官样文章的笑。
“李姐啊,辛苦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我没吱声,拿抹布擦着不锈钢的台面,油腻腻的,怎么擦都觉得不干净,就像这日子。
“退休金都给你算好了,保证让你安度晚年。”
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安度晚年?我那老头子去年摔了一跤,腿脚现在还不怎么利索,家里吃的药就没断过。我儿子小伟,倒是出息,在大城市买了房,娶了媳妇,可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我哪能真指望他。
我这双手,歇不了。
王主任见我兴致不高,又干咳两声,换了个话题。
“这最后几天,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李姐。咱们食堂的规矩,你是最清楚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擦桌子的手停住了。
他这话,意有所指。
我抬起眼,看着他那张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的脸。
“王主任,我干了三十年,什么规矩不清楚?一勺就是一勺,不多不少,保证克数。”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虚得很。
因为有个孩子,我偷偷给他加了三年的菜。
那孩子叫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很高,很瘦,像一根被风随时能吹倒的豆芽菜。
戴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垂着,不敢看人。
他总是在快收餐的时候来,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排在队伍末尾。
轮到他时,他会把饭卡贴在刷卡机上,然后用低得像蚊子哼一样的声音说:
“阿姨,一个米饭,一个免费汤。”
有时候手头宽裕点,会多加一句。
“再……再来半份土豆丝。”
永远是土豆丝,最便宜的素菜,三块钱一份,半份一块五。
第一次见他,是三年前的一个秋天。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食堂里的人比平时少。
他走过来的时候,裤腿湿了一半,黏在细伶仃的脚踝上,那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鞋头已经开了胶。
他照例只要了米饭和免费汤。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却没什么血色的脸,心里莫名其妙地就酸了一下。
我想起了我儿子小伟刚上大学那会儿。
也是这么瘦,也是这么省。
我老公那时候下了岗,我一个人在这食堂里打工,一个月千把块钱,掰成八瓣花。
小伟懂事,每次打电话都说吃得好,吃得胖了。
可放假一回家,下巴尖得能戳死人。
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了省钱,经常一天就吃两顿,每顿一个馒头配点咸菜。
我当时抱着他,眼泪就没忍住。
都是当妈的,见不得孩子受这种苦。
那天,我的手勺抖了一下。
一勺子红烧肉,稳稳当当地落在了他的米饭上。
肉不多,就三块,还带着点油汪汪的汤汁。
那孩子猛地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眼镜都差点滑下来。
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立马把脸一板,凶巴巴地吼了一句。
“看什么看!勺子滑了!不吃就倒了!”
他被我吼得一哆嗦,赶紧低下头,端着餐盘,几乎是跑着走了。
我看着他找到一个最角落的位置,背对着所有人,肩膀一耸一耸的。
是在哭吗?
我心里叹了口气。
这孩子的自尊心,比天还高。
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他照旧踩着点来,要最便宜的饭菜。
我照旧“一不小心”手滑。
有时候是几块烧排骨,有时候是一个大鸡腿,有时候是两勺子番茄炒蛋。
我的动作练得炉火纯青。
舀起一勺菜,手腕在半空中夸张地抖三抖,把多余的肉都抖回锅里,这是做给别人看的。
然后在勺子落到他餐盘的一瞬间,手腕猛地一沉,一拧。
藏在勺子底下的那几块“干货”,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进去。
他从来不说谢谢。
我也从来不承认。
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打菜的窗口,隔着三年的光阴,所有的交流,都在那一勺“手滑”里。
他只是在吃完饭,把餐盘送回去的时候,会路过我的窗口,脚步停顿一秒,然后微微地,几乎看不见地,朝我点一下头。
我也只是眼皮一撩,算是回应。
这事儿我干得隐蔽,但食堂里人多眼杂,哪有不透风的墙。
跟我一个班组的胖婶,不止一次地拿胳膊肘捅我。
“我说李娟,你那勺子,怎么就对着那一个小子打滑?”
我眼皮都不抬。
“帕金森,提前发作了,不行啊?”
胖婶撇撇嘴,没再多说。
她也是个苦出身,知道我的为人,就是嘴上爱占个便宜。
但王主任不一样。
他是那种把“规矩”两个字刻在脑门上的人。
食堂里的每一粒米,每一滴油,在他眼里都是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次,他背着手在后面巡视,正好赶上那孩子来打饭。
我心里一紧,手里的勺子都重了几分。
我眼角的余光能瞟到王主任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正盯着我。
那天我没敢“手滑”。
一勺土豆丝,抖得干干净净,清汤寡水的几根,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显得格外寒酸。
那孩子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端着餐盘走了。
只是那背影,比平时更萧索。
王主任走到我跟前,满意地点点头。
“李姐,这就对了嘛。公私分明,咱们做后勤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个。”
我“嗯”了一声,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张被我翻腾得不耐烦,嘟囔着问:“你烙饼呢?还不睡?”
我把这事儿跟他说了。
老张叹了口气。
“你啊,就是心太软。这大学里穷学生多了去了,你帮得过来吗?万一被人举报了,你这退休都退不安生。”
我当然知道。
可我一闭上眼,就是那孩子瘦弱的背影,和他那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
“我不管,我明天就退休了,我再最后帮他一次。”我赌气似的说。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老张没再说话,只是把他的手覆在我的手上,轻轻拍了拍。
第二天,是我在食堂的最后一天。
我特意起了个大早。
我跟厨房的老刘磨了半天,用自己买的料,在角落里偷偷炖了一小锅猪蹄黄豆汤。
炖得烂烂的,汤色奶白,香气扑鼻。
小伟以前最爱喝这个,说补身体。
我想,那孩子那么瘦,也该补补。
中午开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边是即将离开的伤感,一边是即将“解放”的轻松。
同事们都知道我今天退休,对我格外客气。
胖婶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包她自己做的点心。
“李姐,以后常回来看看啊。”
我眼圈有点红,点点头。
学生们一波一波地涌进来,食堂里瞬间人声鼎沸。
我一边机械地打着菜,一边在人群里搜索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快到收餐的时间了,他还是没来。
我心里开始发慌。
怎么回事?这孩子从来没迟到过。
难道是生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那锅特意为他炖的汤,还用小火温着,香气一阵阵地往外冒。
王主任走过来,看了看稀稀拉拉的学生。
“李姐,准备收工吧。晚上食堂工会给你办个欢送宴。”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眼睛还盯着食堂门口。
直到最后一个学生打完饭,直到食堂的灯关了一半,他还是没出现。
那锅猪蹄汤,从滚烫变得温热,最后彻底凉了。
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沉下去。
心里空落落的。
就好像,我这三年的坚持,这最后的一点心意,变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笑话。
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晚上的欢送宴,我喝了两杯酒。
王主任带头,说了很多漂亮的场面话,什么“几十年如一日”,什么“爱岗敬业的典范”。
我听着,觉得特别讽刺。
他要是知道我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估计会把这些话全吞回去。
宴会结束,同事们把我送到大学门口。
我跟他们一一告别,说了很多“以后常联系”的客套话。
转身的瞬间,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向校园深处。
灯火通明的教学楼,黑漆漆的操场,还有远处那个我待了三十年的食堂。
再见了。
也再见了,那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孩子。
希望你以后,能顿顿吃上红烧肉。
回到家,老张已经给我烧好了洗脚水。
“怎么样?他们没为难你吧?”
“没,都挺好的。”我脱了鞋,把脚泡进热水里,长长地舒了口气。
“就是……那孩子今天没来。”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给我递过来一条毛巾。
“也许,人家毕业了呢?或者找到好工作了,用不着你那勺肉了。这是好事。”
我想想,也是。
他看起来像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三年了,也该毕业了。
是好事。
我应该为他高兴。
可是为什么,心里还是那么失落呢?
退休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清闲,也比我想象的要无聊。
不用再天不亮就起床,不用再闻那一身油烟味,不用再听那嘈杂的人声。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买菜,做饭,给老张熬药,然后坐在阳台上发呆。
儿子小伟每个周末会打视频电话回来。
“妈,退休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挺好的,你爸的腿好多了,我天天给他炖汤。”
“那就好,您也别太累着。钱不够了跟我说。”
“够用,够用。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
挂了电话,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我偶尔会想起那个孩子。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工作了没有,是不是还那么瘦。
时间一长,那孩子的脸在我的记忆里,也开始慢慢模糊了。
只剩下那个瘦高的轮廓,和那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
就这么过了大概一个月。
那天我正在家拖地,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收水费的,趿拉着拖鞋就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西装的小伙子,看着很精神,但我完全不认识。
“您好,请问是李娟女士吗?”小伙子很客气。
“我是,你找谁?”
“这里有一份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他递过来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纸箱,还挺沉的。
我愣住了。
“快递?我没买东西啊。”
小伙子笑了笑:“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送过来的,他特意嘱咐,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上。”
我稀里糊涂地签了字,把箱子搬进屋。
箱子外面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寄件人的信息。
“谁啊?”老张从卧室里探出头来。
“不知道,一个快递,说是有人送给我的。”
我找来剪刀,划开胶带。
心里有点犯嘀咕,这年头骗子多,不会是什么诈骗的新花样吧?
打开纸箱,最上面是一封信。
信封上,是三个苍劲有力的字:
致李娟阿姨。
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个称呼……
我颤抖着手,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信纸,上面的字迹,清秀又有点拘谨。
“李娟阿姨,您好。
请原谅我的冒昧和唐突。
我叫林默,是您三年前‘手滑’打错菜的那个学生。”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是他。
真的是他。
我抓着信纸,手指都在发抖,后面的字,看得模模糊糊。
我擦了擦眼睛,继续往下看。
“阿姨,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这封信,我写了很久,删删改改,总觉得语言太苍白,无法表达我心中万分之一的感激。
三年前,我刚入大学。父亲重病,家里为了给我凑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三百块钱。
在学校里,我每天只敢吃最便宜的米饭,就着免费的汤。我甚至计算过,一个馒头掰成三顿吃,是不是能撑得更久。
我饿,真的好饿。
饿到晚上睡不着,饿到上课头晕眼花。
我甚至想过退学。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食堂里那碗清汤寡水的免费汤,看不到一点油星,闻不到一丝香气。
直到那天,您‘手滑’了。
那三块红烧肉,您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吃到肉。
我躲在角落里,一边哭,一边把那三块肉吃得干干净净,连汤汁都用米饭蘸着吃完了。
我哭,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温暖。
从那天起,您的窗口,成了我大学生活里唯一的光。
您每一次‘手札’,都像是在告诉我:孩子,别怕,这世界还有人关心你。
我知道您是故意的。
您每次都把脸板得紧紧的,凶巴巴的,是怕伤到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我都知道。
我不敢说谢谢,我怕一开口,这个秘密就会被戳穿,会给您带来麻烦。
我只能在吃完饭后,匆匆路过您的窗口,给您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头。
您退休那天,我没有去。
不是我不想去,是我不敢去。
那天,是我大学的毕业典礼。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着像样的西装。
我想去跟您告个别,想光明正大地跟您说一声‘谢谢’。
可我走到食堂门口,又退缩了。
我怕我的出现,会让您为难。我怕别人会因为我,而对您指指点点。
所以,我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谢意。”
我的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都止不住。
老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从后面轻轻抱住了我。
他拿过信,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读着读着,他的声音也哽咽了。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把手伸进箱子里。
箱子里,装得满满当当。
最上面,是厚厚的一摞笔记本。
我随手拿起一本,翻开。
第一页,写着一行字:
“善意账本。”
日期,是三年前的那个秋天。
“九月十五日,雨。红烧肉三块,市场价约五元。”
“九月十七日,晴。宫保鸡丁半勺,含鸡丁四大块,花生米若干,约六元。”
“九月十八日,阴。麻婆豆腐一勺,肉末很多,约四元。”
……
一页一页,一笔一笔。
整整三本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我每一次的“手滑”。
他不仅记下了菜名,还像个侦探一样,估算了每份菜的市场价。
在每页的末尾,他还会写上一段简短的日记。
“今天又吃到了阿姨给的肉,感觉又能多背五十个英语单词了。”
“阿姨今天好像心情不好,没有‘手滑’。没关系,我自己也要努力。”
“今天被王主任看到了,阿姨只给了我土豆丝。我看到她很难过。阿姨,您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批评。我吃土豆丝也很好。”
“考试得了全系第一,拿了奖学金。我第一时间就想告诉您。但我不敢。阿姨,谢谢您,是您让我有力气坚持下来。”
我捧着那几本沉甸甸的笔记本,哭得几乎喘不过气。
我以为我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以为那只是几块肉,一个鸡腿。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沉默的少年心里,这些东西,被如此郑重地记录着,珍藏着。
这哪里是“善意账本”,这分明是一个少年,用他全部的自尊和骄傲,写下的感恩日记。
箱子的底层,还有几个东西。
一个红色的证书夹。
打开一看,是他的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
“林默,建筑系,学士学位。”
照片上的他,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
他不再是那根风一吹就倒的豆芽菜了。
他长壮了,也长高了,眉宇间充满了自信。
证书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建筑模型。
做得很精致,像是一个小区的微缩景观。
模型的最中间,有一栋小小的食堂建筑,门口还立着一个模糊的人影,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勺子。
在模型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
“献给我人生的筑梦师。”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筑梦师?
我一个打菜的阿姨,怎么就成了他的筑梦师?
在模型的旁边,还有一张银行卡。
信的最后一段,写着这张卡。
“阿姨,这张卡里,是我工作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和奖金。不多,但都是我凭自己的努力赚来的。
密码是您的退休日期,六位数字。
我知道,您肯定不会收。您会说,这只是‘手滑’而已。
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手滑’,这是救赎。
您救的,不是我的胃,是我的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希望。
所以,请您务必收下。
这不是报答,因为您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这只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想孝敬一下自己的‘妈妈’。
是的,在我的心里,您早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正式地对您说一声:
谢谢您,阿姨。
祝您,退休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学生:林默,敬上。”
信,读完了。
我抱着那个小小的建筑模型,靠在老张的怀里,放声大哭。
这三十年,我在食堂里,看过无数张年轻的脸。
他们来了,又走了。
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他们的模样。
我只是一个打菜的阿姨,一个在他们青春里,一闪而过的背景板。
我从没想过,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我从没想过,我那一把冰冷的铁勺里,竟然盛着那么滚烫的重量。
老张也红着眼圈,他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值了,娟儿,你这三十年,值了。”
是啊,值了。
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劳,所有的担惊受怕,在这一刻,都值了。
第二天,我拿着那张银行卡,去了银行。
我输入了我的退休日期。
密码正确。
我查了一下余额。
看到屏幕上那一串数字的时候,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二十万。
整整二十万。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拿着卡,手都在抖。
这孩子,他这是把自己的全部都给我了啊。
我立马点了“退卡”,把卡拿了回来。
这钱,我不能要。
一分都不能要。
我回到家,把这事儿跟老张说了。
老张也沉默了。
“这孩子,太实诚了。”
“是啊,这钱我拿着烫手。他刚工作,正是用钱的时候,我怎么能要他的钱。”
“可信上没留电话,也没留地址,你怎么还给他?”
是啊,怎么还呢?
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
突然,我想起了那个建筑模型。
建筑系……
我猛地想起来,小伟的公司,好像就有不少建筑设计师。
我赶紧给小伟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我把林默的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跟小伟说了一遍。
小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能听到他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妈……”他开口,声音有点沙哑,“您……您真是我的骄傲。”
我鼻子一酸。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快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一个叫林默的建筑设计师,刚毕业的。”
“好,妈,您别急,我马上去问。您把他的毕业院校告诉我。”
我看了看证书,告诉了他。
小伟的效率很高。
不到半天,他就回了电话。
“妈,找到了。林默,今年刚入职我们公司合作的一个顶级设计院,因为毕业设计拿了全国金奖,被破格录取的。现在是院里重点培养的新人。”
我听着,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骄傲。
“那……那能联系上他吗?”
“能。妈,您想怎么做?”
我想了想,说:“你把他约出来,我们见个面。我得把钱还给他。”
小伟说:“好,我来安排。”
见面的地方,是小伟公司附近的一家茶馆。
我和老张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心里紧张得不行,手心直冒汗。
这感觉,比当年见儿媳妇还紧张。
老张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别紧张,就当见个晚辈。”
我能不紧张吗?
那可是我偷偷“喂”了三年的孩子。
约定的时间到了。
茶馆的门被推开,小伟领着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走了进来。
那青年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头发剪得很短,显得特别精神。
他一进来,目光就在茶馆里逡巡。
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他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是他。
真的是他。
虽然比记忆里高了,壮了,也自信了,但那副黑框眼镜,那清秀的眉眼,一点都没变。
他快步走到我们桌前,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他“噗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
“阿姨!”
他这一跪,把整个茶馆的人都吓了一跳。
我也吓坏了,赶紧和老张一起去扶他。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他却不肯起,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阿姨,我终于见到您了。”
我拉着他的胳膊,眼泪也跟着掉。
“好孩子,快起来,地上凉。”
小伟也过来帮忙,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拉起来。
他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一个劲儿地用手背擦眼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看着他,心里又酸又软。
我从包里拿出那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
“林默,是叫这个名字吧?这钱,阿姨不能要。你刚工作,到处都要用钱,自己留着。”
他猛地抬起头,连连摆手。
“不,阿姨,这钱您必须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什么心意!你这孩子,你把全部家当都给我了,你自己怎么办?”我有点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我还有。”他小声说,“我工资挺高的,而且院里管吃管住,我花不了什么钱。”
我把脸一板,拿出了在食堂打菜时的架势。
“我不管!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你要是还认我这个阿姨,就把卡收回去!”
他看着我,愣住了。
大概是想起了我当年“凶巴巴”的样子。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卡推了回来。
“阿姨,这钱您不收,我一辈子都心难安。”
我们俩就像打太极一样,把那张卡推来推去。
老张在旁边看着,叹了口气,开口了。
“小林啊,我们知道你是好孩子。这钱,我们心领了。但是真的不能要。娟儿她这辈子,帮过的人不止你一个,她就是这个心肠。要是每个她帮过的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家早就成富翁了。”
小伟也帮腔道:“是啊,林默。我妈这人,你别看她嘴上厉害,其实心比谁都软。你就当了了她一桩心愿,把钱收下。以后,常来看看我们,比给我们多少钱都强。”
林默看着我们一家人,眼圈又红了。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把那张卡收了回去。
但他从随身的包里,又拿出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阿姨,叔叔,这笔钱你们可以不要。但是这个,请你们务必收下。”
我疑惑地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沓现金,不厚,看起来大概一万块钱。
“这是……”
林默说:“阿姨,这二十万里,有一部分是我的奖金,但大部分,是我工作后申请的第一笔信用贷款。我想着,您和叔叔年纪大了,身边总得有点钱应急。”
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这孩子……他竟然为了我,去贷了款。
“那这一万块是……”
“这一万块,是我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不是贷款,是我自己挣的。阿姨,求您了,就收下吧。就当……就当我给您的养老钱,行吗?”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恳求。
我看着那一万块钱,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点点头,收下了。
“好,阿姨收下。但是,下不为例。”
他终于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我问了他的家乡,他的父母。
他说他父亲的病已经好多了,他现在每个月都能寄钱回家,家里的条件也改善了不少。
他还说,他正在设计一个项目,是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建一所新的学校。
“我想让那些孩子,也能有一个温暖明亮的食堂,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茁壮成长的生命。
临走的时候,小伟和林默交换了联系方式。
小伟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你就是我弟。有什么事,随时找哥。”
林默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林默真的像我们的另一个儿子。
他每个周末,只要不加班,都会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和补品来看我们。
陪老张下棋,听我唠叨食堂里的陈年旧事。
他话不多,但总是听得特别认真。
有时候,他会带来他的设计图纸,铺在桌上,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解。
“阿姨,叔叔,您看,这里我设计了一个天窗,这样白天孩子们吃饭的时候,阳光就能照进来。”
“这个食堂的桌椅,我特意设计成圆角的,怕孩子们磕到。”
我看着他神采飞扬的样子,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老张的腿,在林默的各种补品和我的精心照料下,好了很多,已经能拄着拐杖在小区里溜达了。
他说,他得赶紧好起来,以后好帮着带孙子。
因为小伟的媳妇,怀孕了。
而林默,也交了女朋友。
是个很文静的姑娘,也是他们设计院的,看林默的眼神里,全是崇拜和爱慕。
他第一次带那姑娘来家里吃饭,姑娘有点拘谨。
我拉着她的手,给她夹了一大块我炖的红烧肉。
“多吃点,看你瘦的。”
姑娘看了看林默,笑了。
林默也笑了,他悄悄对我说:“阿姨,您做的红烧肉,还是那个味道。”
日子,就像那锅小火慢炖的汤,越来越有滋味。
去年冬天,老张的身体突然急转直下,住院了。
是心梗,很凶险。
医生说,幸亏送来得及时,不然人就没了。
手术费要十几万。
我当时就懵了,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手脚冰凉。
小伟把家里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差五万块钱。
他正准备打电话找朋友借,林默来了。
他二话不说,递给我一张卡。
“阿姨,这里有十万,您先拿着。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看着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孩子,这钱……我……”
“阿姨,”他打断我,“您要是还当我是您儿子,就别说别的。救叔叔要紧。”
他陪着我,在手术室外等了一夜。
老张的手术很成功。
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那天,老张拉着林默的手,老泪纵横。
“好孩子,你又救了我老头子一命啊。”
林默只是笑着说:“叔叔,您快点好起来,我还等着跟您下棋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十万块钱,是他准备和女朋友结婚买房的首付。
我把小伟叫到一边,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这笔钱还给林默。
小伟点点头,他说:“妈,您放心。这笔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还上。林默这个弟弟,我认一辈子。”
老张出院后,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们家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
我把林默给我的那一万块钱,连同他垫付的医药费,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他。
他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收下了。
他说:“阿姨,钱我收下。但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今年过年,我们家特别热闹。
小伟一家三口,加上林默和他女朋友,把我们那不大的小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我做了一大桌子菜。
有红烧肉,有猪蹄黄豆汤,有番茄炒蛋。
都是林默爱吃的。
饭桌上,老张举起酒杯。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但有两个好儿子,一个好儿媳,还有一个好闺女。我知足了。”
我们都笑了。
林默的女朋友,那个文静的姑娘,红着脸,小声地叫了我一句。
“妈。”
我的眼泪,又没忍住。
吃完饭,林默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阳台。
他递给我一个红色的邀请函。
“阿姨,下个月,我和小雅结婚。您和叔叔,一定要来当我们的主婚人。”
我拿着那份滚烫的邀请函,点点头。
“去,一定去。”
阳台的窗外,是万家灯火。
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我刚到食堂工作时的样子。
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不安。
我以为,我这一生,就会在油烟和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平淡地落幕。
我从没想过,我无心的一次“手滑”,会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荡开一圈又一圈温暖的涟漪。
它不仅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也让我自己这平凡得像一粒米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这是一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
它在滚烫的锅边待了三十年,给无数人盛过饭菜。
但只有我知道。
这双手,曾经为一个饥饿的少年,偷偷盛满过一整个春天。
本文标题:妈妈想陪女儿上大学当上食堂阿姨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39295.html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